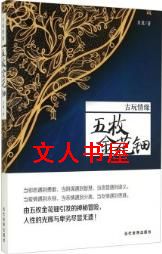花钿笄年-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一个姑娘家,本不该去,可又信不过不成器的兄弟们。只有咬着牙进了胭脂胡同。
春福堂下,一个皮条客和她谈好了价。簪子递出的一刻,苏浴梅心里说不出的凄凉。祸不旋踵,天上竟掉下一件东西,无端砸到她。所幸并不严重,她抬头看,楼上灯光幽暗,看不清窗口的人。她想,算了吧。
庭于希说不清站了多久,直到窗外只剩下黑漆漆的夜。回过身,郁棠似笑非笑朝他摊开一只手。
“什么?”
“讨赏啊,谢媒钱。”
几天后,媒人踏破了苏家门槛。媒婆们摇唇鼓舌说得天花乱坠。
苏太太不动声色:“我听说,你们师长娶过亲了。”
“战乱中没了,都好几年的事了,也没留下孩子。”
“你听着,我苏家虽穷,可也是诗礼传家,簪缨世族。一介武夫,年纪大了近十岁,我苏家姑娘绝不给他续弦!”
苏太太大声吩咐:“关门送客!”
消息带给庭于希,他正在马厩。
归陵高牵过缰绳:“这是土尔扈特王刚送来的马,选了最好的留给您。”
庭于希暴跳如雷,一枪撂倒这匹纯种阿尔登马:“捎话过去!三天后,花轿进他苏家的门,抬不来活的,就给我抬死的!”
第 3 章
三、媒婆把话捎到苏家,苏太太险些晕了过去。
苏浴梅说:“妈,我去。”
“太委屈了你。”
“嫁给谁还不都是嫁。”
“我知道你懂事,可是……你的心事,妈心里有数。”
“妈……”
“你都快二十了,这么多年来,妈挡了多少提亲的,就是知道,你心里……”
“别再说了。”
“本想着,全禄一回来,就把你们的事办了,偏偏摊上这档事。”
陪房何嫂进来说:“太太,黄少爷来了。”
苏太太马上擦擦眼角。
黄全禄兴高采烈的进来:“伯母,浴梅!”
苏浴梅强颜欢笑:“怎么这样高兴?”
“我在地方法院谋到职了!”
“全禄!”苏太太突然抓住他的手,“你带浴梅走!”
“这是怎么了?”
苏浴梅皱起眉:“妈——”
“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被那个军阀糟蹋!”
黄全禄着急:“究竟怎么了?”
苏太太抹眼泪:“如今,北平街头巷尾,谁不知道,谁不议论这件事!苏家的脸面都丢尽了!”
末了,黄全禄说:“放心,我绝不会让浴梅受委屈,我先回去打点一下。”
他走后,苏太太心安一些。她拉着女儿的手:“庚子年,西太后西逃,那些清兵,不知道抵御外侮,反倒洗劫民宅;丁巳年,张勋的辫子军复辟,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总之,历朝历代,当兵的哪有好人?比洋人还坏!”
“我明白。可是,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你和爸爸怎么办?那个人不会善罢干休的。”
“浴梅!”苏太太狠下心,“你要是嫁给他,就是坏了苏家的门风,妈现在就自缢你面前!”
第二天,媒人过来,箱箱笼笼摆了一厅。按照苏家旗人习俗,门户贴、年庚贴、迈书龙凤贴,以及‘掐笼’、酒海、如意匣,小定大定的吉物一日全齐了。街坊们探头探脑聚着看。苏太太只觉得丢了体面,又忧心。
黄全禄傍晚才过来,神情不定。苏太太看他只身没带行李,心里更急:“怎么了?”
“伯母,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这么多年在国外,不知道北平的事,你看看。”他指着一张誊写的日本《朝日新闻报》。
苏太太看,上面写着‘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那个庭于希,名噪一时,连日本人都怕他,我们平头百姓根本惹不起!”
“你不是学法律的?这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宋哲元是北平代市长,二十九军的军长。庭于希去赌,他就开支票,庭于希逛妓院,他就给派卫兵!我们找谁说理去!”
“你的意思,是不愿意跟浴梅一起走?”
“这是……是私奔啊。我怕,怕伯父面上过不去,怕浴梅跟着我受委屈,更怕……”
“更怕误了你的大好前程!”苏浴梅不知什么时候走出来。
“浴梅——”黄全禄一脸委屈。
“浴梅——”苏太太心如刀割。
“什么也别说了。庭于希,我嫁!妈,您雇窝脖吧。”
第三天.归陵高亲带人送来六十四抬全副妆奁。满顶银的‘星星冠轿’配着‘锣九对’全副执事。苏太太没出门,苏父喜滋滋站在街口,觉得面上很有光彩。
庭府装葺一新,宾客满堂。庭于希一身戎装,马靴铎铎。
媒婆问归陵高:“大喜的日子,师长怎么还穿军装?”
归陵高冲墙上努努嘴。一副对子,‘未靖四夷驱倭寇,不卸胄甲洗征袍。”
“这是我们师长入士官学校前,吴玉帅亲手题赠。不收复东北,师长绝不脱军装。”
“还好苏老太太没来,她最不喜当兵打仗的人。”
拜完天地,宾客们闹酒。在座有上司,有同僚,都是军政要员。纷纷举杯。庭于希几杯下肚:“小归替我吧。”
“庭师长海量,别留着一手!”
“于希,再来几杯,好日子,尽性!”暂编师师长刘汝明近前递酒。
“酒后失态,我怕吓到人家姑娘。”
“老弟!你也会怜香惜玉了!”
平日里,豪赌阔饮,庭于希毫不含糊,可真沉下脸来,别人也不敢勉强。军参谋长打圆场:“春宵一刻值千金,你们别浑搅和了!”
喜娘扶着凤冠霞帔的苏浴梅,正要进去。庭于希快走几步,将她拦腰抱起。
众人喝彩起哄声中,他横抱着她,走进洞房。
四、苏浴梅揭了盖头坐在床边。喜娘端过点心:“新娘子先垫垫。”
满盘子的子孙馍馍、龙凤饼,苏浴梅随手捡了块水晶糕,咬了一口放下。
庭于希伸手抬起她的下颚。
苏浴梅瞥他一眼,忙又垂下眼帘。这几乎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他。
喜娘斟满合欢酒便退下。庭于希一饮而尽。苏浴梅喝不得酒,可事已至此,唯有矫情镇物,她也饮尽。
庭于希眼里略带赞许,摊开的手里已多了一支簪。苏浴梅眼前一亮,她当掉的花钿镶珠点翠簪!
他把簪插进她发髻:“以后,你喜欢什么,我都会给你。”
她坐着没动,他又拔出那支簪,顺手解开她的长发。
苏浴梅心里很清楚,嫁给他,她认命。坐进花轿,她没留一滴泪,那么现在,她也不会怕。更何况,酒力不自胜,醉在他怀中,‘芙蓉帐里奈君何’……
庭于希什么也没说。这个南征北战的军人,双手早被枪把磨出厚厚的茧,那样有力那样风情的抚摸在她柔软的肌肤上。
她承欢在他身下,为感官上的臣服而羞愧。
他太懂女人,他那样耐心那样细腻,他究竟有过多少的风流韵事。她心底微微愠意带来的迟滞,在他看来,是纵情后的‘无力慵移腕’。他意识到有些失度,揽她枕在自己胸口。
苏浴梅是被家中佣人唤醒的,阳光已丝丝透入帷帐。新婚妇实不该起得这样迟,她红着脸穿好衣服,随着马嫂来到前厅。
厅中供着主位,庭于希跪在案前。听到声音,他起身看了眼马嫂:“让她睡吧。”
“不合规矩阿……”
苏浴梅脸又红了。
庭于希点好香,递给她:“给我爹娘上柱香吧。”
她照做了。
归陵高进来:“报告!”
“说吧。”
“张参谋长刚打电话来,说……”
“好了!”庭于希喝止,“我现在就去。”
他拉起苏浴梅:“这个家里没什么规矩,有访客,你应酬一下,我不在家时,照顾自己。”
归陵高叫备车,跟着他走出去。庭于希问:“日本人又有动静?”
“今年四月以来,他们频频演习,这是这个月第三次了。”
“哼!他们演,二十九军的刺刀也不是吃素的!”
“军长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叫您立刻去丰台。”
“这些都是军事机密,以后不要在家里说。”
“是是。”归陵高搔搔头,“一下多了这么些人,我有点不习惯。”
庭于希一走,屋子一下冷清了。苏浴梅想,也好,他和她,几乎还是陌生人,他不在,反倒自在些。
无事可做,她闲步在这座两进二十几间的四合院。佣人们看见她,恭恭敬敬唤声‘太太’。她和气的回应,心里很清楚,'奇+书+网'这不过是附骥攀麟得来的尊重。
书房里摆着各式奖状,青天白日勋章分外显眼。衣柜里挂满一年四季咔叽布的军服。苏浴梅想,她拴不住一匹不羁的野马,注定寂寞,注定一生颠沛流离。
不过,她是个安常处顺的人。架上有书,案头有纸,她还想在院落中饲鱼鸟,天井旁植槐榆,寂寞,不是不能打发。
夕阳完全消失在影壁上。苏浴梅一个人吃晚饭。庭于希正在百里外的宛平城,泥里水里摔打。苏浴梅想,他不知又逍遥在哪个女人的温柔乡。
宛平演习一结束,二十九军连夜紧急会议,直至第二日傍晚。秦副军长也已疲惫不堪:“先回去休息,明日一早,团籍以上将官,随我去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
归陵高打开车门,庭于希被一位参议拉住:“去哪里?”
“回家,睡觉。”
“睡觉么,何必回家。明早还要集合,进城也不方便。”
庭于希笑笑,坐进车。
“金福寿。十八盏灯的排场,几个烟泡下肚,包你什么乏儿都解了。”
“我不好这个。”
“特地从皮条营请了万紫红姑娘坐堂,怎么样?兄弟做东。”
“改天吧。”庭于希吩咐司机,“开车。”
车开远,归陵高问:“回家么?”
“百顺胡同,清吟小班。”
“师长,跟您这么久,原来您喜欢南班子,难怪那个什么万紫红您看不上眼。”
庭于希疲倦的靠在车座上。
五、车停在清吟小班外,庭于希几乎睡着了。
鸨母认得他的车,迎出来:“您多久不来了。”
“忙。”
“今天来,是看哪位姑娘?”
“你们这儿,江南糕饼是一绝。给我一斤水晶糕,火候要足。”
“您……不叫姑娘啊?”
“以后吧。”
“哎呦!这一来二去的,姑娘们都等老了。”
“凭你们的手艺,就是改行作点心,不会输给正明斋。”
坐回车里,归陵高问:“糕饼哪都有,何必特意拐到这儿?”
“南方点心,北方做不出那种味道。那天,她吃了一口就放下了。”
“她?谁啊?”
庭于希微笑不语。
苏浴梅听见门外靴声,翻身面向里。
不一会儿,庭于希进来,带进一阵呛人的烟味。
苏浴梅皱了皱眉,黑暗中他看不到。她感到他掀被上床,躺在她身后。然后,他略带胡茬的脸蹭上她的后颈,一只手绕过她的腰,伸进衣服的缝隙,抚摸。
这让她难以忍受。他一走两天,一句话也不交代。回来就如此恣意。
她向里挪了挪,庭于希却更加放肆。她忍无可忍,稍用力一挣。他缓缓松开,翻动几下,并没再纠缠。等她转过头看,他竟已沉沉睡去。苏浴梅呆了呆,眼泪悄悄滑下,这只是她新婚的第三夜。
早晨起来,庭于希照例不在,她已习惯。外间桌上放着一包东西,绢帕裹着。马嫂说,师长落下的。
苏浴梅打开,里面还有油纸,似乎包着吃食。她留意到那帕子名贵的质地,绣着字:‘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清吟小班’。
刺鼻的脂粉气令人晕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