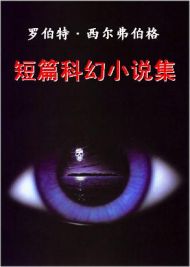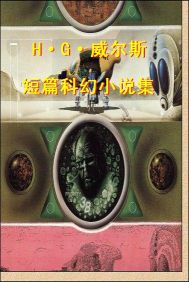短篇小说(第八辑)-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失了……
大概是因为这顶帽子,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是过去英国老派绅士的必备品,
现在正古怪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他说过,他径直地走了过来,朝着这顶帽子,在冷
清的站台,黑呢帽是最醒目的存在,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顶帽子开始的,我像一
件莫名的飞行物,必然地降临在这场相遇之中。他是谁,我是谁,年龄,身份,地
址,电话号码,为什么坐上这趟火车,我们彼此一无所知,我们彼此毫不相干,可
我们是那么的投机自在。是的,一无所知,除了他内心的迷惑,焦虑,他的秘密隐
私,他存在之外的存在,他都不假思索,他都直言不讳。在抵达黑夜之前,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窗外的灯火如流星划过,好像有薄雾升起,车厢显得特别的明亮,我
们就这样肩靠着肩,坐在一片明亮之中。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一丝微笑在嘴
角如同光的一闪,我的第二次提问显得更加虚弱难堪,是有些差错已经超出了我理
解力的范围,他一定开始厌烦我了,我说对不起,他又笑了,淡淡地,我陷入了手
足无措的境地。
火车到站了。
怎么,没人来接你,他这才注意到我两手空空的,没有任何行李。我说出了我
要去的那个偏僻的地方,他说还有四个小时的长途呢,现在恐怕没有班车了。一些
起起落落的光斑影点在他的脸上晃动,人流在往出口涌动,只有我们滞留在这当中,
本来属于我的担心和焦急,转移到他的身上,我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此行真正
的目的变得清晰起来,我渴望那种危险向我逼近,那种决定越来越强大,站台已经
空了,我的眼里布满欲念。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由他来安排,这个陌生
的男人。
他把我带到一家小酒馆,要了一个羊肉火锅,两瓶啤酒。小店雅致洁净,油画
效果的印刷品点缀在墙上,偶遇,男人,火锅,酒,热腾腾的肉香,都具备了某种
装饰性的意味,在我贫乏的年纪,一览无余的神情,一个人,没有任何障碍,我该
挥霍这一切,我想。是不是冒险,这样的冬夜,我本该像所有同龄的女孩那样,穿
着丝绸睡衣,躺在温馨柔软的单人床上,读琼瑶的小说,记住每一句奶油蛋糕式的
情话,入梦,自己成了书中的女主角……遗憾的是,我从来不读琼瑶,我喜欢尼采,
我的男朋友也喜欢尼采,他揭开我衬衣纽扣的时候,我们在说尼采,他拉下了我牛
仔裤的拉链,我们依然还在说尼采,我已经被他剥光了,我竹笋般鲜嫩的身体呈现
在月光下的时候,他说,让尼采见鬼去吧,我说,这不公平,我也要看你。他迅速
地脱掉裤子,第一次目睹成年异性的下体,骄傲而神气。我们接吻,慌乱地,笨拙
地企图把事态引向更深的层次。没有想象中欢愉,我的舌头被咬住了,疼痛别扭,
以致怒火中烧,我说,你也见鬼去吧,我把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从我身上掀开。某
个夏夜的校园草坪上,虫子的欢叫响成一片,晚风吹过,我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来自我两只大腿之间,我身体的核心部位。
碗里堆满了羊肉,金针菇,粉丝,吃得越多,饥饿感反而越浓厚。啤酒的味道
清淡纯正,此刻,我蒙受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可以幸福地死去。你看,我都告诉你了,
我毫无羞耻地说出了一切,你呢,你的第一次……我努力在扮演一个引诱者,我的
诱饵是我相对幼小的年纪,我显得开放而率真,我有一百个理由去放任自流,在无
聊又无助的日子里,我希望岁月的痕迹像新大陆一样浮出时间的大海。他会识破我
的伎俩吗,这伎俩里装着什么。他吃得少,喝得少,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我,眼神深
邃,深不可测的深,是的,是的,这样的眼神几乎覆盖了我对那次晚餐的全部记忆。
他的笑容不再,他的沉默取代了刚才的喋喋不休,正如车厢里的浅笑,同样让我手
足无措。我永远跟不上他的速度,沮丧慢慢地围拢过来。我的脸很烫,灯光和酒让
我看见了漫天飞霞,沮丧里面包裹着的兴奋,眩晕,让我的勇气和胆量变得声势浩
大。我回应着他的目光,僵局终于被打破。他这样描述自己:那是大雪天,我们迷
路了,很冷,在一间被遗弃的破房子里,我们紧紧的抱在一起。是冲动,取暖的冲
动,想融化在彼此的身体。多么滚烫,是她的血,我非常感动。我哭了,我认定会
永远永远地爱她,就是我刚才向你说过的那个女人。我在夏夜,他在雪地,竟有如
此巨大的差异,这一定和季节有关,现在现在,也是冬夜,我的脸很烫,可我的身
体是冰凉的,冰凉的身体特别特别的想……
波德莱尔说,爱是什么呢,爱迫使心卖淫。
那么,以后呢,以后呢,在那样的年纪,对故事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生活本身。
我很想知道他和那个女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件是如何展开的,如果不发生点什么,
活着和死去就没有多大的差别。比如,我买了那顶帽子,这是一个信号,比如我的
莽撞出走,一定会在一个看不见我的地方,隐藏我同时又呈现我。非常固执的想法,
我在迁就我的想法,我被它所蛊惑。趁我还没有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趁我的想象
力还如洪水般泛滥,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你们又在一起了,经常幽会,瞒着你
的妻子,你没有愧疚,她本来就是你的,是你未竟的事业,那个过去的你和现在的
你并行不悖,你来来回回地坐火车,从这里到那里,体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你
成了钟摆,懂得平衡,匀速,滴滴答答,你被时间宠爱,流逝的正在返回,返回的
正在演进……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坐在了一家小舞厅,人很少,慢三步的曲
子没完没了。一些稀疏的人影在音乐里摇晃,还有我和他,相拥着,仿佛一个虚构
的意象在移动。鼻子里是小羊皮的味道,棕色皮衣手感柔滑,我的前额靠在他的肩
头,继续揣度故事的边际,揣度另一个女人的容貌,疲惫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降临的,
我完全忘记了引诱和被引诱是这次出走的真正主题,我被别人的故事弄得心力交瘁。
一次没有发展好的艳情,在适合它发展的地方,梦一般地夭折了。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幸运,你只说对了一半,男人语调低沉,属于他的忧伤,
他的柔情都与我无关,我们是怎样坐在一起的,太富有戏剧性,太强烈,反而显得
不可信。唯一可信的是他的声音,他的绵绵不绝的述说。是的,我们重新开始了,
我们约定每星期见一次。是她的提议,我无法拒绝,我不能抗拒她的哭泣,尽管流
泪的眼睛不再明亮。我们分手后,她经历了两个男人。两个男人都先后离开了她,
她始终没有弄清自己错在哪里。她现在很富有,是两次离婚带给她的补偿。在她豪
华的住宅里,我们做爱。我解开她真丝衬衫的纽扣,我急于想恢复从前的记忆,那
双花蕾般明媚的乳房,一直驻留在我对她的思念里。幻觉终究是幻觉,现在,蜷缩
在我怀里的身体是如此的陌生,因为创痛,因为时间的侵蚀,变得黯淡。我还是尽
力去迎合她,其实是为了迎合我的记忆,我正徒劳地抵御时空制造的残忍,抵御遗
忘,我相信爱是精神的,是不可磨灭的,是可以用行动去挽救的。我在欲望里陷得
越深,我的悲哀就越浓厚。雪白的丝棉床罩,雪白的家具,北欧风格的简约造型,
我以为又回到了那个同样雪白的夜晚,那是怎样的洁白啊,泛着淡淡的幽蓝的光—
—身体的起伏,光在颤抖,在她纯洁的肌肤上滑动。血管和血管的对接,像水溶解
在水里,没有断裂,没有缝隙,没有疏离,没有冷却,我紧紧地闭上眼睛,是那道
白光,铺天盖地的白……第二次,第三次,当我的幻觉渐渐涌退,我毫不犹豫地承
认了自身的失败,我发现爱是不可重复的,重复的爱,爱的复制品是人对自身的欺
妄,必须面对不想面对的结束,毁灭,有一种痛苦永远无法补偿,也不需要补偿,
它一直在那里,在爱隐退的地方,怜悯就出现了,我是在怜悯她,我想安慰她,我
什么都可以给她,除了爱。可我依然不心甘,那样的情感为什么要出现,出现又消
失,我被这个问题所纠缠,正如为什么要出生,出生了,又不得不死去。
我说过,我永远跟不上他的思维,我的无聊的企图,在他莫名的复杂的思绪面
前溃不成军,怎么去想,怎么去做,都是错。我捕捉不到他的故事,我原以为省略
了许多世俗的过程,那情景瞬间就可以降临。我不知道该如何终止这一切,我的即
兴发挥,我的拙劣的故事编码,还没有出场,就被他用传说的利箭击倒。我想是我
的运气不好,碰上了一个奇怪的对手,而不是合谋者。
亚恩。凯菲莱克说:这种包含着爱情,无能为力和死亡的混合体,把我激怒了。
当然,我没有放弃,我年轻的骄傲的心不允许我放弃。我们又走进舞池,我柔
软地靠近他,借用了狂蜂浪蝶的姿态,什么故事,阅历,岁月痕迹,我可以通通不
要,我只要一个庸俗的结果,叶尖上的露珠,阳光里的尘埃。身在旅途,就该具备
旅途的狂野。否则,我无法告慰我的躁动,从我出发的那刻时,潜伏在我身体深处
的躁动。我纸片儿一样地贴过去,纸片儿一样的轻薄,光滑的地板留不住脚印,影
子也留不住,影子都飘了起来,我听到了他湿热的呼吸。他一定感觉到了我倾斜的
重量,那种要倒下去的,渴求搀扶的动向。他的手臂紧张起来,有力的紧张,善解
风情的手臂,肌肉的暗语,秘密就深藏在那里,属于所有男人的秘密,旅途中的男
人,嗅到了狐媚的气息,他的心有没有狂跳,他的心还在何处漫游。《加洲旅馆》
的旋律升起,中速,滋生了中年人怀旧的毛病,忧郁总是缠绕不清的。故事被休止
符拦住,节奏有点吞吞吐吐,还有现场演唱的喧闹声也被录进了唱片,一圈又一圈,
唱针,唱盘,唱片以及我们,在某种范围之内,目标突然消失了。如果能隐姓埋名
地死去,最好就是现在。
我们走向旅馆。
标准间,两张单人床并列着。没有谎言,甚至他还给妻子拨了电话,道了晚安,
他还不合时宜地说起了女儿,说女儿在少儿芭蕾舞赛得了奖,一只纯粹的小天鹅。
我取下帽子,脱掉外套,他继续说,孩子会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斜卧在床
边,眼睛里有光,大概是台灯的映照。墙角的落地灯射向屋顶,如强光下的面容,
肌肉的抽搐,皱纹的走向被放大,有些狰狞。最微弱的是壁灯,小小的一块光区蜷
缩在那里,整个房间就这样被光线切割成一片一片的领地,领地的主人就是那盏发
光体。门和窗紧闭,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空间,任何主题,任何欲念,任何情绪都可
能被撕扯,也许突然断裂,也许悬若游丝。比岩浆的流动还缓慢,那灼热浓稠的液
体,是怎样抚过粗砺的地壳,从深深的黑暗中渗透出来,非常固执,非常专注,心
乱了,慌乱的乱。我说我感到头晕,想吐,我没有孩子,头晕想吐就是现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