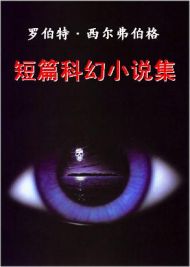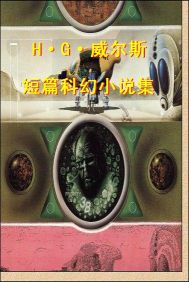短篇小说(第十九辑)-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放门或是玄武门实在是太远了。我现在只有沿原路返回;进入另一条岔道再试
试。我心中焦急;手忙脚乱;挡道的荆条毫不客气地在我脸上拉了一道血痕;很疼。突
然间我有点恍惚起来。树林幽深;视野中的景物显得迷离;不可捉摸。我像在梦游。
小径也许在无意中拐过了一个角度;和不远处的围墙成了平行状态;看上去永远不会
重合。我沿着小径一直往前走;像一个梦中的巡视者。我这是在干什么?
不知不觉中;我终于走到小径的尽头。围墙立在我前面;上面布满苔藓植物。墙
角下有一垛砖;阳光透过树林;在上面投下凝固的斑点。
对任何事情你都不能抱过于确切的期望;譬如那扇铁门。但转机也是会有的;那
堆砖头就是一个例证。你找不到这里面的逻辑。它分岔了。樱洲的岔道就更多。它
们纵横交错;和夹拥的冬青配合着;把不计其数的樱花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冬青很茂盛;有半人高;如果不打算从上面翻过去;你常常就要在樱洲兜圈。樱洲以樱
花而得名;但此时看上去满目绿叶;花已经全部凋谢了;只有草皮上的花瓣还在提示
人们;它们也曾爆炸般地开过几天。但仲春已不是樱花的季节。
游人们也已经散了。樱洲本就是玄武湖最偏僻的一个洲;除了樱花;还有什么呢?
樱花盛开的日子还有些恋人们到这里来;现在花期已过;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呆在这儿。
脚下的这条路伸向樱洲的深处。常来樱洲的那段日子我和女友经常在这里散步。樱
花下的草皮其实很好;但女友不愿意坐下来。她是个很懂得爱惜自己的人;如果忘了
带一张旧报纸;她就宁愿一直走着。说来可笑;我们从来也没有忘记那一盒权当门票
的香烟;却总是忘记带报纸。现在是我一个人。脚下卵石小径的缝里钻出了一簇簇嫩
绿的小草;离去的游人给它们留下了生长的缝隙;也给鸟儿们留下了一个自在的天空。
几只斑鸠在樱洲的两侧彼此呼应着;悠长而凄凉。
翻墙而过时;我曾经很慌张。但现在我倒不那么急了。这也许是一个有意义的聚
会;应该像我接到的通知那样郑重其事。可是我觉得;我见了他们很可能会无话可说。
此前我曾通过那个心脏移植者提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下那个为我们提供器官的年轻
人的父母。结果人没有约齐;只有我和“心脏”一起去了。那是个很普通的家庭;家
境一般。我们只见到了老太太;还有墙上她儿子的遗照。那是很青春的一张脸啊。我
说不清我的感受;喉头有些发紧。“心脏”和我在同一家医院手术;我们应该算是认
识的;可我没看出他是个饶舌的家伙。我想心同此心;他的感情应该和我类似;但他话
太多。他夸老太太的儿子;还说自己现在非常好;除了要定时吃药;简直达到两匹马力
——他的名字就是马力——“您看;我现在上楼一点都不喘!”他那语气有点像是用
了人家的什么物品;来告诉人家使用感受。老太太淡淡地听着。她也许原本有很多话;
但轮不到她说。马力说得高兴;一会儿称老太太为母亲;突然又一溜嘴喊老太太“祖
母”;让人摸不着头。他解释说:“您儿子是我们的母体;您不就是我们的祖母吗?”
老太太苦笑了一下;脸色有些变了。她绝口没提她的儿子;只在分别时要我们不要忘
了吃药;“好好过”。出了门我和马力分手;我的泪水突然流了出来。我的泪浸泡着
角膜;火辣辣的。不久以后我又单独去过一次;但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大片的空地将建
成汉中门广场;上面植着一些据说是从樱洲移去的樱花树。
这几天一直在刮风;时断时续。风渐渐大了。从北方刮来的春风挟带着烟尘在天
空呼啸而过。天有些发暗;树木轻轻摇晃着。我现在是个耳聪目明的人。我能看见无
数的粉尘从天空落下;又被卷起来;受惊的鸟儿尖叫着弓箭一般在林间弹射。我脸上
被树枝划破的地方有点疼;紧绷绷的。已经两点半了;我对这次聚会产生了一丝畏缩
情绪。从墙上往下跳时;我的脚崴了一下;更糟的是;裤子被墙上的钉子划破了;破洞
处漏出了口袋。口袋是白色的;很显眼。我没想到一个裤子的口袋竟然有那么大;好
像我是漏出了里面的大裤衩。也许有人还会因此而联想到一个拖着蛇皮袋的拾荒者。
想到这个我宁愿在樱洲再转转。如果不是考虑到回去还要再翻墙我真想马上就走。
他们来了吗?在哪里?通知是那个“心脏”马力的手笔;他话多;写了满满一页;却
没有说明准确的地点。我知道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个外地人;为了方便;他们大概会在
樱洲的小石桥那儿等。地上有一张报纸;飘着飘着;被冬青挡住了。我忍着脚疼追过
去拣了起来。我打算拿在手上;挡一挡那个破洞。我现在已经走到了樱洲的南边;远
处的湖面传来了隐约的水声。风紧一阵慢一阵;随着风声的减弱;灰尘从天空飘落下
来;我的嘴里有些发涩。这是来自远方的尘土;不知道从樱洲掠去的灰尘现在又落到
了哪里。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春天的沙尘暴和我的生活有着一种隐秘的联系。这倒不
是怨天尤人。每年春天;四处漂浮的花粉都会弄得我两眼发红;咳嗽不止。后来在樱
洲;也是这样的天气;我和女友从樱洲回去;带回了导致我手术的眼病。最后一次的樱
洲之游就像是一段模糊不清的影片的开始。银幕上人影憧憧;周围一片黑暗。在影片
的结尾;她离开了我;我被推进了手术室。这是一个俗套的故事;但俗套本身也许就是
逻辑吧。如果不是那次手术;我现在就不会到这里来;如果没有那最后一次樱洲之游;
我即使得眼病;甚至动手术;但可能跟今天的聚会却未必有关系。是的是的;这真的是
缘分。除了马力;我和其他人没有联系。据马力说;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是一个女教授;
有五十多岁了。做肾移植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很漂亮;另一个是年轻小伙子;上海人;
写小说;还做收藏生意。马力告诉我;这个人很有办法;在艺术圈子里他是个生意人;
买单总是他抢着去;可到了生意场上他又自称自己是个艺术家;很清高。
马上就要见到他们了。我找个地方坐了下来。右脚很疼;好像肿了。我皱着眉用
力捏着脚腕;脸上的伤痕被牵得发疼;我此时的表情一定很狰狞。我得收拾一下。我
小心翼翼地走到水边;撩起水擦了一把脸。风不紧不慢地刮着。沙尘暴带来的阴霾已
经消散;天空明亮了些。我回到刚才坐过的地方;却发现报纸已不知去向。我四处张
望着;像是在找报纸;又像是找聚会的那几个人。已经三点了。我这么晚露面恐怕难
以避免地要成为他们的话题;这是迟到者的常规待遇。但我既然来了;总是要见他们
一下的。对他们一年来的生活我也有些好奇。老太太让我们“好好过”;我是女友跑
了;工作也丢了;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我绕过拦路的冬青;慢慢向小石桥方向走去。
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发出一阵动静;哗啦啦乱成一团。我怔了一下。草丛中探出一个脑
袋;上面顶着几根草屑。是一只狗;狐狸犬。它抬起亮亮晶晶的小眼睛看着我;突然又
没入草中不见了。
这时候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小石桥的南面有一块草坪;几个人围成一圈;一个
男的站着;另有一男两女坐在地上。站着的是马力。他正说着什么;我听不清。风中
的声音断断续续。鸟儿们先是怯怯地叫;彼此鼓励着;忽然起了劲;一下子聒噪起来。
我现在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视网膜巩膜玻璃体是我的原件;角膜却是别人的遗赠。
那个年轻人;他家在本市;想必生前也到樱洲来过的吧。水边的树丛中又传来了斑鸠
忧郁的叫声;声声慢;使我感觉到一丝寒意。他来过的;一定来过的。一年后的今天;
有几个人各自带着他的遗赠;又来到这里;可是他再也不来了。我有些伤感。我的视
线透过角膜透过枝桠伸向前方。这时我意外地发现了那只狗。它兴高采烈地在几个
人中间绕圈子;仿佛在走着梅花桩。年轻女人抻手按住它;把它搂在怀里。马力说着
话;手在用力比划……我现在上楼都不带喘的;他指点着环岛的卵石路;我可以绕着樱
洲跑几圈给你们看看!他们都说我现在是两匹马力;二马力!我在家正是老二;你们说
巧不巧?
他的话被一阵嘎嘎的笑声打断了。是那个长头发。如果不看仔细点;你可能会把
他误认为女人。想必他就是那个艺术家。我也忍不住想笑;马力的话简直就像是我们
去老太太家拜访时的翻版。他说;我现在清闲了;忙到头了;每天就是下楼上班;上楼
回家;上楼下楼还不喘;你说是不是轻松?坐在地上的年轻女人问:你还在上班?干嘛?
马力道:看大门。其实就是看报纸。那些小青年说我现在是一不做事;二不休妻;人
生最佳境界。他的话把几个人都逗得笑了起来。马力问:你呢?年轻女人道:我肝不
好;没你好。我好;我好什么呀!马力叹口气;现在酒都不能喝了。以前应酬多;现在看
大门……什么?你还喝酒?一直没有插话的女教授突然问。我不喝了;马力说;动过手
术后就喝过一次;结果是一塌糊涂地动山摇;倒到桌子下面去了。
我觉得很有趣。他又说了一个“一”。那只小狗也汪汪叫起来;好像它也识数。
我沿着冬青树悄悄往前走了一段;坐了下来。裤兜里的香烟倒是没有丢;我拆开来;却
没有火;只好拿一根在鼻子上嗅着。医生叮嘱我抽烟对眼睛不利;我已经戒了。现在
我很想抽。再抽上恐怕就难戒了。一发;一发而不可收拾残局;瞧瞧;我也“一”了。
那边老教授奇怪地问:你怎么会把成语连起来说;一啊一的?马力说:酒席上学的啊。
还有呢;——还有什么的?长发艺术家说:一技之长短不拘;一孔之见多识广;一举两
得陇望蜀;一石二鸟枪换炮;艺术家讲得忘形;站起身来;双手比画:一箭双雕虫小技;
一触即溃不成军;一命呜呼风唤雨;还有一唱雄鸡天下白痴!
众人都有些发懵。马力说:你们那儿也玩这个?艺术家说:哪儿不一样啊。女教
授问:你们喝酒就说这个?这说的是什么?马力说:这叫一字令。年轻女人“嘁”一
声道:男人!艺术家理理长发;道:也有说女人的呀;你很漂亮;一顾倾城门失守;再顾
倾国将不国。男人!年轻女人又哼了一声。女教授道:这是说男女还是说政治?艺术
家道:哪里哪里;我说的是自己。他捶着腰自我解嘲道:我现在完了;只剩一个肾了。
嗨;真是一触即溃不成军了。没有人接他的话。马力大概是看年轻女人不高兴;把话
题岔开去。我们现在都算是残疾人了;以后要多多联系;肝胆相照。女教授说:我做
的是肝移植;谁做胆移植?胆不需要移植;割掉就是了。年轻女人的话有点冷。
我坐在树丛中;腿有些发麻。我已经决定就在这里坐下去;一直坐到他们散时我
再露个面就行了。那边的女教授这时提出要走;她站起身;说她的命是拣来的;她手上
还有很多事情。谁不是呢;他们几个在挽留她。艺术家说:再坐坐吧;既然来了。我
还要坐火车呢。马力说:没关系;让你的腰友送你去车站。我听了一愣。那边艺术家
哈哈大笑起来:对对;我们是腰友。我们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