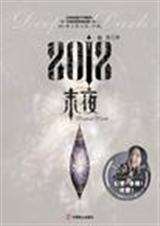123 雷·布雷德伯里中短篇科幻小说集-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克拉丽丝说道:“你介意我问你一些问题吗?你当消防员已经多久了?”
“从二十岁就开始干了,十年前的事了。”
“你看过你烧毁的那些书吗?”
他笑了。“那可是违法的!”
“噢,当然。”
“那可是个很棒的工作。星期一烧米莱,星期三烧惠特曼,星期五烧福克纳,把他们烧成灰烬,连灰也要接着烧。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口号。”
他们继续往前走。女孩又问:“很久以前,消防队员是灭火的而不是放火的,这是真的吗?”
“不是。房屋向来都是防火的,相信我的话。”
“奇怪。我曾经听说,很久以前的房子会突然着火,需要消防队员去给它们灭火。”
他大笑起来。
她迅速扫了他一眼。“你为什么要笑?”
“我不知道。”他又开始笑起来,接着止住笑。“怎么啦?”
“你笑的时候我并没有说什么好笑的事情,而且你回答得很快。你从不停下来想想我向你提的问题。”
他停住脚步。“你很古怪,”他说道,眼睛看着她,“你不知道要尊重别人吗?”
“我并不想冒犯你。只不过我喜欢仔细观察别人,我想。”
“那么,难道这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吗?”他轻拍了一下451 这三个绣在焦黑色袖子上的数字。
“有,”她轻声说道,一面加快了脚步。“你有没有看过喷气式汽车沿着那条林荫道赛车?”
“你在转换话题!”
“我有时候想,那些开车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草、什么是花,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慢条斯理地看过它们,”她说,“如果你把一团模糊的绿色给开车的人看,他会说,哦,没错!那就是草!一团模糊的粉色!那是玫瑰园!模糊的白色是房子。模糊的棕色是奶牛。有一次,我的叔叔在公路上开得很慢,一小时四十英里,他们把他监禁了两天。那不是又滑稽,又让人伤心吗?”
“你想得太多了,”蒙泰戈有些不太自在。
“我很少看‘电视墙’,也很少去看比赛或者去游乐园。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来琢磨一些疯狂的东西,我想。你看见城外面竖在乡间的那些二百英寸长的广告牌了吗?你知道以前的广告牌只有二十英寸长吗?但是车开得太快了,所以只好把广告牌拉长,这样才能让他们看见。”
“我可不知道!”他突然大笑起来。
“我打赌我还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早晨的叶子上挂着露珠。”
他突然记不清楚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这让他焦躁不安。
“如果你抬头看”——她冲着天空点点头——“会看见月亮上面有个人。”
他已经太久没有看过月亮。
剩下的那段路上他们一言不发,她若有所思地静静走着,他则在局促不安的寂静中向她投去探究的目光。到她家的时候,他们发现房子里灯火通明。
“发生了什么事?”蒙泰戈很少看见房子里亮那么多灯。
“噢,只不过是我的父母和叔叔围坐在一起聊天。这种情况跟成为步行者一样,只是更少见些。我的叔叔又被捕了——我跟你说了吗?——因为他是个步行者。哦,我们这种人很独特。”
“你到底在说什么?”
她笑了起来。“晚安!”她开始朝前走。接着,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走回来,用充满疑问和好奇的眼神看着他。“你快乐吗?”她问道。
“我什么?”他大声说。
但是她已经走了——奔跑在月光中。前门轻轻关上了。
第三章 一次奇妙偶遇
“快乐!无聊之极!”
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把手放进前门的掌形凹槽里,让它识别触摸。前门缓缓开启。
我当然快乐。她在想些什么?我不快乐吗?他询问寂静的屋子。他站着,抬起头看客厅里空调上的格栅,突然想起格栅后面躲藏着什么,此刻似乎正在窥视他。他迅速移开目光。
真是奇妙夜晚的一次奇妙偶遇。他不记得自己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只除了一年前的一个下午。那天下午,他在公园里遇到一位老人,和他聊了聊……
蒙泰戈甩了甩头,看着一堵空白的墙壁。女孩的脸就在墙上,记忆中的她的确非常漂亮:事实上,是美得惊人。她的脸缥缈而单薄,仿佛半夜醒来看时间时,黑暗的屋子里那面依稀可辨的小小时钟的钟面——时钟在苍白的寂静中闪着微光告诉你几点几分几秒,它有一种无所不知的确信,知道该如何向你讲述这个匆匆而逝堕入更深的黑暗、随即又奔向新一轮红日的夜晚。
“什么?”另一个蒙泰戈问道;这个潜意识中的白痴总在疯狂地呓语,他独立于意愿、习惯与心智之外,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他又瞥了一眼墙壁。她的脸还酷似一面镜子。真有点不可思议;你又认得几个可以把你的光芒反射到你自己身上的人呢?人们通常更像——他在寻找一个比喻,最后终于在与他工作有关的事物中找到一个合适的——火把,在熄灭之前熊熊燃烧,释放出耀眼的光芒。有多少人的脸可以洞穿你,之后又把你的思想、把你内心最深处那些令人颤栗的想法回掷到你的身上?
那个女孩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她像是个观看木偶戏的热切观众,在戏开始之前,就已经预见到眼睑的每一次眨动,双手的每一个动作,手指的每一次颤动。他们在一起走了多久?三分钟?五分钟?但是现在看来那段时间仿佛十分漫长。在他眼前的那个舞台上,她的身形显得分外高大;她那苗条的身体在墙上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他觉得倘若他的眼睛有点痒,她就会眨眨眼。倘若他下颚的肌肉有些微的抽动,她就会在他之前早早地打起哈欠。
为什么,他思索着,为什么现在想来,她好像就是在那里等我,在那条街上,在这样深的夜里……
他打开卧室门。
仿佛是在月落之后走进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冰冷阴森的陵墓。一团漆黑,没有一丝外面银色世界的痕迹;窗户紧闭,像一个都市喧嚣无法穿透的墓穴。房间里并非空无一物。
他侧耳倾听。
空气中飘荡着嗡嗡的低响,如蚊翼鼓动般不可捉摸,那是一只躲在暗处的黄蜂发出的电鸣声,此刻它正舒适地窝在它那与众不同的粉红色温暖巢穴之中。音乐声大到几乎可以让他听出旋律。
他感到脸上的微笑慢慢溜掉,像油脂一般渐渐融化,往下流淌;像蜡烛燃烧太久之后,那原本华美的外形开始软化变形,最后连火焰也熄灭了。黑暗。他不快乐。他不快乐。他对自己说。他认识到这才是事情的真相。他把快乐当成面具戴在脸上,但是那个女孩拿走了他的面具,穿过草坪跑远了;而他也无法上前敲开她的门,再把他的面具要回来。
没有开灯,他站在黑暗中想象卧室里的情形。他的妻子躺在床上,身上没有遮盖,全身冰凉,好像一具放在坟堆上的尸体;眼睛紧盯着天花板,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细钢丝连接起来,眼神木然,一动不动。她的耳朵里塞着精巧的海螺状无线收音机,各种声音、音乐谈话、谈话音乐以电波的形式,潮水般一浪又一浪地涌向她那清醒的大脑——那未曾入眠的沙滩。卧室里确实空荡荡的。每个夜晚,电波穿过墙壁,声浪如海潮般向她袭来,把整晚不曾合眼的她冲向黎明。过去两年里,米尔德里德没有一个夜晚不畅游在那个海洋中,没有一次不欣喜地沉浸在那片汪洋大海中。
卧室里冷冰冰的,他感到难以呼吸。但是他不想拉开窗帘,也不想打开落地窗,因为不愿意让月光照进来。于是,伴着那种再过一小时就会因缺氧而死的痛苦感觉,他摸索着走向他那张空荡而阴冷的单人床。
在他的脚踢到地板上的东西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踢到一个东西。这种感觉与他差点转过弯撞上那个女孩时的感受极为相似。他的脚朝前发出声波,声波遇到前方的小型障碍物后又反弹回来;他的脚虽然仍然悬在空中,但还是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了返回的声波。他一脚踢中了它。它发出一声钝响,在黑暗中滚远了。
他笔直地站立着,在这个分外寻常的夜晚,倾听着黑暗中那个躺在床上的人发出的响动。她的鼻息非常微弱,仿佛只能搅动生命最为遥远的边缘——一枚纤小的树叶,一根黑色的羽毛,或者仅仅是一根纤细的发丝。
他仍然不希望有外界的光芒。他抽出喷火装置,摸到刻在银色圆盘上的火蜥蜴,轻轻一按……
他的手上窜起一朵小小的火苗,两枚月长石在火光中看着他;那是两枚沉在溪水深处的苍白的月长石;五光十色的生命随着清澈的溪水流淌,但却无法触及溪水深处的石头。
第四章 米尔德里德
她的脸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岛屿,岛上可能会飘雨,然而她的脸上却没有一丝雨意;云层可能会把它们的浮影投向岛屿,然而她的脸上却感觉不到影子。只有紧塞在她耳朵里的无线电收音机仍在嗡嗡作响,她的眼睛如玻璃般空洞,她的呼吸轻柔而微弱,空气在她的鼻孔中进出,而她似乎并不关心它是进还是出,是出还是进。
方才他一脚踢开的东西此时在他的床脚边闪闪发光。那是一个用来装安眠药的小水晶瓶。今天早上瓶里还装着三十枚胶囊,但是现在已经空空如也,水晶瓶敞着口躺在小小火苗的微光之中。
他站在那里,屋顶上的天空突然发出尖叫。震耳欲聋的撕扯声,仿佛有两只巨手正从接缝处扯下长达上万英里的黑色长线。蒙泰戈好像被切成两半。他感觉自己的胸膛已经被砍下撕成碎片。喷气式轰炸机接二连三地飞过,一架接着一架,一架接着一架,一二,一二,一二,有六架,有九架,十二架,一架又一架,一架又一架,都在为他尖叫。他张开嘴,龇着牙发出一声狂啸,所有轰炸机都停止了尖叫。房屋震颤。手上的火苗熄灭了。月长石消失了。他感到自己的手猛地伸向电话机。
轰炸机已经消失不见。他感到自己的嘴唇在动,轻轻擦过电话听筒。“急症医院。”传来一声含糊的低语。
他感觉星辰已经被黑色喷气轰炸机的巨响震成粉末,早晨起来就会发现地上盖了一层星粉,仿佛下过一场奇异的雪。他站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脑子里转着这些愚蠢的念头,嘴唇继续不停地嗫嚅,嗫嚅。
他们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实际上,他们有两台这种机器。其中一台滑进你的胃部,仿佛一条黑魆魆的眼镜蛇钻进深不可测的古井,在里面找寻积存多年的死水和堆积于井底的悠悠岁月。死水微澜,缓缓翻腾,它吸干了那些漾到水面的绿色沉淀物。它能吸食黑暗吗?它能吸干年复一年沉淀下的毒液吗?它默不做声地吞食着,间或因为里面的气闷和黑暗中的盲目搜寻发出一些声响。它有一只眼睛。表情冷淡的操作员在戴上一个特殊光学头盔之后,甚至可以洞穿那个正被机器抽空的病人的灵魂。眼睛看到了什么?他没说。他可以看,但是他看不见眼睛看见的东西。整个手术过程就好像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一条沟渠。躺在床上的女人只不过是他们在挖掘过程中碰到的坚硬的大理石层。继续,不管怎样,把钻往下推,给空处填上泥浆——如果这条颤得厉害的抽吸式眼镜蛇还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