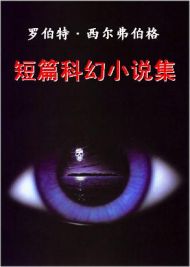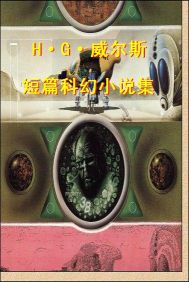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一)-第1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共同点。她告诉我说,她小的时候也很孤单,她的共感现象也令她的父母非常头痛。正如她所说,“在我们发现这件事的真相之前,他们一直认为我有点疯癫。“她说完这话,放声大笑了起来,但是我可以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她受过的伤害有多深。
“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我?”我问道。
“只对我的医生。”她说,“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虽然比较罕见,但是他也听说过这种现象。听他这么说,我才如释重负。”
这番话让我楞了好一会儿,因为斯图灵医生跟我说过,他在医学文献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安娜的话与医生所说的有些矛盾,提醒我她的存在并非真实,但是我很快从脑中驱走了这种想法,继续和她的谈话。
那天晚上,我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喝光了带回来的三杯咖啡——当然,她也一样——就这样,我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我们谈着各自的生活,我们的创作理想,我们的未来之梦。我们发现我们的通感体验非常相似,我们感官印向的转换常常产生相同的结果。例如,我们都觉得新割下的草的味道呈圆形,汽车的喇叭声会使我们尝到柑橘的味道。安娜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偏好钢琴艺术和古典音乐。在我向她说明我是打算如何构架出那首赋格曲错综复杂的结构时,她突然低头看了看她的咖啡杯,然后抬起头来说,“哦,真糟糕,我的咖啡没了。”我低头看看我的,发现刚才我已经喝干了第三杯咖啡了。
“明天中午见。”她说着,她的影像开始淡去。
“好的。啊我大声叫道,生怕她听不见。
之后她便成为一个幻影,一阵气体,一份思念。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干瞪着对面厨房的墙壁发呆。她走了,我好长时间都坐立不安。我喝下的那些咖啡在血液里狂奔,我虚弱的体质从没受过如此的“刺激”,我的双手在颤抖,我知道觉是睡不成了,因此在这平房小小的房间里绕圈踱步了一个小时后,我便坐了下来搞我的赋格曲,看看这会儿能做些什么。
我立刻抓住了头绪,就从星期六被困住的那个地方开始。此刻,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明镜般地玲珑剔透。当我用各种颜色表达音符时,甚至听得到音乐声,似乎我正在一边制作出录音片段,一边播放录制进去的内容。我疯了似的工作,速度又快,一点儿错也没出,所有的音乐上的难题此刻都迎刃而解,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所作的每一个决断都充满了灵性。最后,约在早晨8点左右时(太阳升起来我都没有注意到),咖啡对我身体造成的伤害开始发作,我觉得恶心得很,胃里翻江倒海,头痛欲裂,这种痛苦实在太折磨人了。10点时,我开始呕吐,吐过后感觉稍好了些。上午11点,我出现在小餐馆里,有买了4杯咖啡。
女服务员想引起我对早餐的兴趣,我说我不饿。她说我看起来气色不好,我勉强对她笑了笑,好让她放心。她却追问我怎么了,我冲她发了一顿火——我记不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了。然后她终于明白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咖啡。我拿着我的宝贝直接走向海滩。那天风和日暖,清新的空气使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些。我坐在沙丘中间一个很深的低凹挡风处,坐在那里饮着咖啡,看着安娜作画。不管她在哪里,她总是在专心画她的画,衣服很大的彩色抽象画。偷偷地看了她几分钟,我突然意识到,这幅画的构图,以及色调的搭配在我眼中看来就像是弗朗兹·舒伯特的作品,《b小调第八号交响曲(未完成)》的乐谱。开始时,我觉得这很好玩,想想看,我的音乐知识竟然在她的世界中得到延续,我的想象竟然是那个世界的来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我对弗朗兹·舒伯特的一点小小的兴趣,竟然会自己表现出来。我在想,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这个想象出的世界中的素材。这个想法掠过我的脑海,给我沉重的打击,我不想这样,我要她与我完全不同,她有她独立的实体,否则她与我的友谊又算是怎么回事
?我摇摇头,想甩掉这个想法。中午时分,她出现在我的身边,就在这些沙丘中间,而我那时已经忘掉了那个讨厌的想法。
整个白天我们都在一起说说笑笑,沿着海边散步,在尖岬岩石上攀登。下午3点左右,咖啡快没有了,我又返回了小餐馆再买些。我跟他们买了整整两壶,然后直接倒入那种很大的外带塑料容器内。女服务员没说什么,只是摇摇头。当我在这里忙我的事时,安娜也在她的那个世界里,准备好一大桶的咖啡。
我们在平房里再度见面,当傍晚来临,我们隔着厨房里的一张桌子,拿出各自的作业一起研究。有她在,我的音乐灵感有如火焰在燃烧,而她也告诉我,她第一次发现了整体的构图,这正是她一直在努力突破的方向。我太沉醉于我的工作之中以至于头也没抬就伸手去拿我的蜡笔,可到手的却是一枝紫罗兰色的彩色粉画笔。我没有这种颜色的笔,安娜有。
“瞧。”我对她说,在这一刻我感到一阵晕眩,视神经又开始痛了。
她把目光从画作移到我的手上,看见了那根紫罗兰色的粉画笔。一时之间,我们都静静地坐着不动,为这事代表的意义所震撼。慢慢地,她的手越过桌子向我伸来。我也丢掉粉画笔,把手向她伸出。我们的手碰到了一起,我可以发誓,我感觉到我的手指和她的手指缠绕在了一起。
“这意味着什么,威廉?”她略带恐惧地说着,放开了我的手。
我站起来的时候差点失去了平衡,抓住椅子靠背才站稳了。安娜也站起来,但当我向她走过去的时候,她却不住地往后退,“不,这不对头。”
“别害怕。”我小声地说,“是我。”我踉跄着向前移动了两步,我与她离得是如此之近,甚至可以闻到她身上的香气。她退缩着,但没有走开。我伸开双臂抱住了她,试图吻她。
“不。”她叫道。她的两只手用力地推在我的胸脯上,我向后跌倒在地。“我不要这样,这不是真的。”她说着,开始匆匆忙忙地收拾她的东西。
“等一下,对不起。”我急忙道歉。我双腿乱蹬,想站起来。彻夜不眠,几加仑的咖啡因,紧张得要崩溃的神经,此时就像赋格曲中缠绕在一起的多重声部搅在一起,让我头痛欲裂,像是被马蹄重重地踢了一下。我的身体在发颤,视线开始模糊起来,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一会儿清醒,一会模糊。我硬撑着不让眼睛闭上,看见安娜转身,似乎要从客厅里走出去。我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用家具作支撑物,跟在她的后面。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猛地一下打开小屋的正门,尖声呼唤着她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发现躺在海滩边,不省人事。小餐馆里的那个白胡子老人每天早晨都要道海滩上溜达一阵,于是便看到了我。警察接到报警后来了,暖融融的太阳,玫瑰古朴的香气,透过窗户洒在我身上。
他们让我在那间小小的海边医院多待了两天,好看看我神经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常。一位精神科医生来看了我,我成功地说服了他,让他相信我是因为要完成学校的作业,用功过度才导致这样的后果。显然,小餐馆里的女服务员已经告诉过警方,我喝了大量的咖啡,而且量大得简直不可理喻,又一直没有睡觉。这些话显然也传到了来给我看病的医生的耳朵里。当我告诉他这是我首次尝试喝咖啡,因此才昏死了过去,他便警告我不能再喝那玩意儿了,他告诉我老头发现我倒在自己吐的一大摊污物里。“你的体质显然不适合喝这东西,你昏迷期间很可能会因窒息而死。”
我谢谢他的忠告,并向他保证,以后我一定远离咖啡。
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我试着进一步思考发生在我和安娜身上的事情。显然,我大胆的举动吓坏了她。今后还要不要去打扰她为好的念头掠过我的脑海。在医院里,回想起当时发生的一切,我可以肯定,我确实已经可以与她进行身体上的接触了,但这一事实却令我十分不安。我开始怀疑起斯图灵说的话了。也许,我们认为是通感现象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只是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我以为是否再找她?先不去考虑这个。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再见一次面,至少要为我的卤莽行为道歉。
我问护士,我在海边屋子里的东西是否被带到医院里来了,她告诉我是的。在医院里的最后一天,我早早穿戴好,花了一整天等待出院通知。那天下午,他们给我把东西拿来了,我仔细地翻查,但是,我的赋格曲蜡笔画乐谱没有了。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有什么东西。其他每一样东西豆子,惟独没有那张大的画图纸。我让我的护士——她非常和蔼,不知怎么使我想起了布瑞丝尼克太太——帮我再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带给我的。查了以后她告诉我没有其他东西了。我打电话给瓦里奥尼岛警察局,先感谢了一番,顺便再问问他们是否看见了我的画。答案是肯定的。我的赋格曲凭空消失了。我知道它的消失很快就会让我居丧不已,但当时确定了之后我稍微有点麻木,甚至还为自己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
我决定回到父母的家里去住几天,恢复一下,然后回音乐学校继续我的学业。在医院附近的汽车站等车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小报摊上去买了一包口香糖和一份报纸,以消磨时间。
我的目光在糖果架上扫视时,突然停留在一样东西上,我想当时自己的样子肯定就像夏娃第一次看到苹果一样。那是一袋汤普森牌咖啡味硬糖。看到袋子上的字样后,我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我的腹腔神经开始不安分,我的手掌心开始冒汗。包装纸上写着,“不含咖啡因”。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运气如此之好。我紧张地看看身后,买3袋。一上车我就扯开了一包,由于用劲太大,结果有一大把都散落在座位上和走道上。
我乘坐出租车到了父母的家里,我得自己开门进去,他们的车不在家里,我想他们今天出去了,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都有点想他们了。夜晚降临了,他们还是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我猜他们也许出去度一个短假,他们经常出去度假的。这没什么。我走到自己在家里的老据点——钢琴前的长椅,坐了下来,开始嚼吃那些咖啡风味的硬糖,直到吃累了,再也不详坐在那里熬夜为止。我躺到小时侯睡的儿童床上,像小时侯睡觉时一样,脸对着墙壁,很快就睡熟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从坐长途车回家又熬了夜的我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到了下午,对于我的赋格曲的命运的怀疑得到了确认。这种糖果不能像冰激凌那样给我带来安娜的清晰影像,更比不上黑咖啡,但它的成形效果已经足以让我追随她一天的活动。我看见了,她将我的那张蜡笔画乐谱作为她的期末习作交了上去。她是如何将它拿走据为己有的,我不知道。这不符合逻辑。我飞快地瞥了一眼这幅作品,试图看清楚自己是如何将主题和答题拼凑在一起。如果我能再多看一秒,我就能听见乐谱发出的音乐声,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它,以理清这篇乐曲错综复杂的结构。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