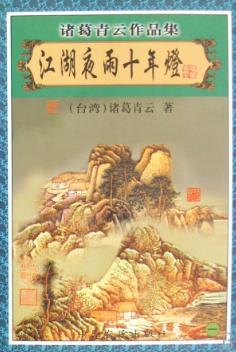夜雨霖铃-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谈和。
谈和不就表示没事,阿玛和大哥哥会回家,一切又会恢复常态吗?
攸君还不懂大人复杂的世界,她坐在窗前,看着愈来愈黑的天空,雨又渐渐地落下,花儿一朵一朵地被打到台阶上,落叶残红乱成一片。
吴攸君……无忧君,她向来如她的名字般无忧地虑,然而,在这一天之内,她突然体悟到李清照那首“声声慢”中的凄凉意味。
守着窗儿,独白怎生得黑!
梧桐更是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她虽然才十二岁,但内心的恐惧,一点儿也不比大人少呀!
天全黑了,府里不似平日,没有巡夜的守卫,没有往来的嬷嬷、奴仆,没有处处点燃的灯光,四周静得犹如老天扣下了一个大盖子,把一切都遮掩住了。
唯有雨声,滴滴落落地打在叶上,令人觉得心慌。
刑部的人让厨房送饭来,吃过饭后,仍等不回额娘,毕竟还年幼的攸君,就在荧荧的烛光中,恍惚地睡去。
但她睡得并不安稳,脑中还充满各种声音,内心也布满疑惧,像是人好疲累,但魂仍清醒,姜嬷嬷她们低声的话语,一句句地隐约传来。
“据说咱们这公主府本来就不吉利。”春棋说:“它在明崇祯时候,住的是一个叫周延儒的宰相,他在这里自尽,还死了不少妻妾,冤气可深啦!”
“当初就有人对额驸爷说过,可他就不信这个邪!”姜嬷嬷说:“他那人目中无鬼神,胆大包天,我就猜迟早会出事的。”
“我听管家婆婆的丫头说,去年初,咱们后院石井的那块地,几次出现狐仙,去问卜都说是灾祸,公主还为此和额驸爷闹,额驸爷回说是妇人之见,一点都不予理会……”珊瑚也说出自己的听闻。
自尽、冤气、凶邪、狐仙、灾祸……这些词,在这特黑、特阴的夜里,形成了某种诡异的氛围。
攸君眨眨眼,在一片灰蒙蒙中,她仿佛看到两个白影子朝她走来,飘飘地不似人,檐下的雨滴滴落落的,竟是鲜红色的血……
是噩梦!攸君想要尖叫,远处却传来巨响,像山崩地裂般,惊得人仿佛要魂飞魄散。
姜嬷嬷要去查看,却被门外的士兵阻止。
攸君下了床,用命令的口吻说:“这是公主府,没有人可以挡本格格!”
她往前面的大厅冲,士兵们也不敢去抓她,姜嬷嬷、春棋和珊瑚又拿斗篷又拿纸伞地跟在后面。
果真是有事发生了!平日绝少开的中门,此刻竟大敞着,两具漆黑透亮的棺材就放置在大厅前方。
姜嬷嬷倒提一口气,惊慌地把攸君往怀中揽,“格格,你别看!”
攸君是吓坏了,但她随即想,这棺木里的人又是谁?它们往公主府送,表示是公主府的人吗……
突然,外面响起急乱的马车声,声音几乎还未止歇,入宫一日的建宁长公主便由中门跌爬地奔进来,直到来到两具棺木前,她瞪大眼睛,一副要昏厥的样子。
送棺木回来的刑部官员恭谨地说:“公主,额驸爷和大阿哥已在今日寅时就刑,请节哀顺变。”
“不——”长公主凄厉地发出一声长嚎,在这静夜里更教人不忍卒听。
她冲到棺木前,扯开覆住的白布,看见那紧闭眼的尸身,一边一个,都是她至爱的人。
她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剧痛,大哭地说:“苍天呀!我的夫、我的子,你们罪不及死呀!为什么要如此狠心,为什么要赶尽杀绝……”
这二十一年的婚姻,就如一场梦,全部化为乌有。建宁长公主想到这几个月来所受的人情冷暖,以往爱护她的人,全都转过身去,连皇额娘也不例外,她求呀求的,哭着求、跪着求,皇额娘竟只是丢给她一句——
“你和额驸爷日日同床共枕,世霖又是你的骨中肉,你竟连他们要造反也不知道?你管不了他们也就罢了,总不能当个又瞎又聋的糊涂人吧?!”
吴应熊和汉人来往过密的事,她早就知道,但他是个极爱热闹的人,身在举目无亲的京城,总不能连交朋友的权利也没有吧?还有……世霖,和他父亲一个脾气,根本还是个孩子,又懂什么造反呢?
他们全都是为朋友所累、为吴三桂所累,没道理要他们牺牲生命吧?!还说什么为留全尸,只绞不斩,可恶不仁的朝廷,竟让一个二十一岁的孩子来杀他的姑丈和表弟,就只因为他是皇上吗?
建宁长公主哭得声嘶力竭,心中忿忿不平,抚着棺大喊,“苍天呀!先皇明鉴呀!这是您当年给女儿许的婚姻呀!那时,我不想嫁给应熊,是您逼我嫁,嫁了之后,现在又硬被逼得当寡妇……您不该替我作主吗?您在天之灵能心安吗?”
管家婆婆见建宁长公主有些半疯狂了,便走过去提醒她说:“公主,我明白你心里难过,但别忘了太皇太后的话,哀痛要有分寸,别失了礼仪。”
“你们不如也杀了我吧!”建宁长公主哭嚎地说。
攸君偎在姜嬷嬷的怀里,早已泣不成声。她看到管家婆婆那怕事的模样,忙奔过去推她说:“你让我额娘哭,别挡她,也别挡我!”
这时,攸君看到了棺木中的父亲及哥哥,他们穿戴得十分整齐,没有血,没有伤口,面容一切如生前,仿佛只是闭着眼睡觉而已。
也许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并没有死,阿玛仍可以和她对背唐诗,世霖哥哥仍会教她养鸟、玩蛐蛐儿……攸君愈想愈有可能,于是动手去摸尸体,“起来!起来!你们都装死,只是要唬弄我的,对不对?”
她这个举止,吓坏了所有的人,管家婆婆和姜嬷嬷都连忙上前制止她。
攸君挣扎地叫道:“额娘,阿玛和大哥哥没有死,对不对?”
建宁长公主以泪眼看着小女儿,哀痛的将她紧紧揽入怀。
攸君哭着说:“额娘,你叫他们起来好不好?”
听到女儿一连串令人心酸的质问,建宁长公主的情绪反而逐渐平静下来,强忍着依然绞痛的心,她一字一字的说:“准备灵堂,点亮长明灯,立刻烧纸钱,请人来裁白布……还有超渡念经的师父。”
“回公主的话,处理葬仪的人及念经的和尚尼姑,都已经在门外候着了。”刑部官员说。
建宁长公主望着几乎被她遗忘的刑部人马,冷冷的,充满辛酸悲愤地说:“你们可真周到,真是送佛送上西天啊!”
“这是皇上的恩典。”刑部官员说。
难道还要她谢恩吗?建宁长公主只是冷哼一声,站在两具棺木间,听着攸君哀哀的哭声,看着纸灰扬起,她的泪扑簌簌流下,量已是无声。
一切就如一场梦,不是吗?她荣华富贵的四十年、她富丽堂皇的公主府。此刻在她眼里,不过是一片废墟。大水冲溃、山石压塌,由无到有,似乎……似乎没有一件是真实存在的。
世间事,终是枉费呀!
今年春天的雨真多,缠缠绵绵地下个不停,公主府闭户守灵,一室凄清的悲风让攸君感受到没完没了的沉重,几乎忘记外面的世界。
她有多久没听见笑声了?仿佛永远永远……
“小格格,你晚餐又没有吃,这怎么可以呢?”姜嬷嬷走进房间说。
“我额娘吃过了吗?”攸君问。
姜嬷嬷好半晌没出声,一会儿才又叹口气说:“现在连吃口饭对她而言都是酷刑呢!”
“对我不也是酷刑吗?”攸君说。
“嗳!小格格,全府都闹翻了,你可别再人小鬼大了。”姜嬷嬷说着,突然像想到什么,翻了翻口袋,“瞧!这里有两串铃子,是我在衣箱里找到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大哥哥的?”
提到“大哥哥”,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伤心。攸君接过来说:“这是前些时候去靖王府,征豪和洵豪送我的。”
算算已是三天前的事了,那时的她多快乐,能够自由来去、自由玩笑,不像现在,成了黑户,失去父兄,没有人理睬。
征豪和洵豪会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呢?芮羽舅妈会不会不再疼爱她了呢?
又一阵悲戚漾满攸君的心底,她轻抚着串铃子,埋首在被里,好希望一觉起来,噩梦就能彻底消除。
攸君就在雨声中睡去,不久又被打更声吵醒。
“嘘!”有人在她耳旁说。
她的身体被腾空抱起,攸君开始慌乱的挣扎,但四周实在太黑了,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姜嬷——”她设法想叫人。
“嘘!小格格,是我,蒋峰。”来人低声说。
蒋峰是阿玛的贴身侍卫,向来很宠她,以前老是给她当马骑,后来则不时由琉璃厂买些小玩意儿来讨她的欢心。
攸君知道是他,安心了不少。
蒋峰带她来到后院,天气凉飕飕的,但至少雨已歇止。
“我们要去哪儿呢?”攸君不解的问。
“找你阿玛和大哥哥。”蒋峰淡淡的回答。
“胡说,我阿玛和大哥哥已经死了。”攸君懂事地说。
“他们没有死,正在别处等你呢!”他说。
所以,棺木里的人真的是装死的?攸君有些郁闷的心,像是突然又见到阳光般的开朗起来,“那我额娘呢?额娘怎么不和我一块儿来呢?”
“她要晚一些才会到。”他避重就轻的说。
他们现在身处在最荒僻的石井处,攸君突然想到狐仙的传说,觉得有些害怕,手一松,串铃子掉到地上。
“那是什么?”蒋峰问。
“串铃子,快找给我,不能丢的。”攸君急急地说。
蒋峰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子,找到一团金属物,再交给攸君。这时,远方似乎有人走动的声音传来,他见情况紧迫,忙拿出一方沾有蒙汗药的巾帕,罩住攸君的嘴。
攸君在失去意识之前,听到他说:“小格格,这是为了你好。”
接着,攸君经过许多地方,由京城里到京城外,只是她毫无知觉,已完全没有记忆。
等刀子清醒过来时,已在某处陌生的郊野,见不到没死的阿玛及大哥哥,也见不到随后就来的额娘。
这全是蒋峰策划的,他为攸君担心,怕攸君因拥有吴家人的血统,最后会难逃一死。
“我带你去找你爷爷。”他说。
攸君自然是又哭又闹,但天地如此之广,她才十二岁,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哪有选择的余地呢?
她就这样离开了额娘、公主府,及十二岁以前的种种,唯一留在她身上的,只有征豪送给她的串铃子。
那铃声总是提醒也,康熙十三年的春天,紫禁城带着花香味的细雨,仿佛极远极远的召唤,却也一年比一年模糊……
言妍……夜雨霖铃……第二章捕捉
第二章捕捉
忧心耿耿,
寄桐叶芳题,
冷枫新咏。
莫遣秋声,
树头喧夜永!
——史达祖·齐天乐
铃声叮当,叮当,叮当……
攸君恍惚间似又回到石虎胡同那幢深宅大院,有长长的咽廊、曲折的石桥、假山下的荷花池……不!这不是梦!她是真的走在里面,双脚踏地的感觉如此的真,手也确实触碰到那些壁柱……
蓦地,她睁大眸子,清晰地来到眼前的是竖横着纱质帐幔的屋宇,雕刻着一朵朵大花的格窗,正透着黎明晨曦的光。
梦里不知身是客……李后主的这句词,真是说尽了许多飘游之人的心事。
她最怕在这个时候醒来,日月交移之际,真假难分之间,人就会显得特别脆弱,过去及现在混沌成一片,抓不到,却寸寸刨空她的心。
这里不是北京,而是湖南的衡州。
此时不是康熙十三年,而是康熙十九年。
她不再是十二岁的小格格,而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