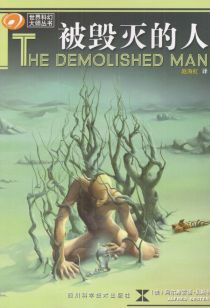好管闲事的人-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寒伧处,但他在他自己的脸貌上的自信,等于零。他又从一些过去经验上找那因相貌
不扬为人瞧不上眼的证据,这恋爱,他就似乎已经看得明明白白,是在女人第一面的印象
上破坏了。
悲哀着,如同为这还未曾恋的失恋预兆悲哀着。这样也是在另一时有过的事,不是第
一次!
若不知道住在对窗隔一丈远近的房子里是一个年青女人,则他坐在桌边的意义当另是
一种意义。那时纵有一些恋爱的情绪,燃烧着心子,当是那离得很远很远的渺茫的薄薄无
望的悲哀情绪。在自己幻想的恋爱上来失恋,还可用目下工作来抵抗这不落实的遐想。如
今则明明在一个女人身旁,而又似乎明明遭女人拒绝,他把这失败原由全放在自己不大方
的相貌上,一个样子不敢自信的人,在未经女人选中以前,就先馁了这希望,无法啊!
他愿意在假设中把自己的长处补足了不标致的短处,这长处总以为并不缺少。且将另
外一个生得极丑的麻脸男子得好女子垂青的榜样保留,以为自己假使办得到,则自然是可
以照例成功的事。然而那朋友,所补救的是一个剑桥的硕士头衔,与将近二十万元的遗产。
他有什么呢?这时代,已进化到了新的时代,所有旧时代的千金小姐怜才慕色私奔的事已
不合于新女子型,若自认为在标致上已失败落伍,还不死要爱新时代女子的心,则除了金
钱就要名誉。他的名誉是什么?一个书铺可以利用他赚钱,一个女子则未见得有这样一 个
情人引为是幸福。一个杂志编辑者,在同他要稿子的信上,可以客气地称他为先生,朋友,
一个书铺在他卖书广告上,可以称他为天才,名家,——然而这不能算做抵得过一个情人
或一个丈夫的资格。反之凡是作这一门事业的年青人,在实际上许多人可以享受的实惠,
这类人却因了工作上把性格变成孤僻无用,应付思想中的问题俨若有余,应付眼前一件小
事却彷徨无措,恋爱则更容易居于失败地位了。并且除了那少数中少数的女子,真需要爱
情,其余多数的女人,她们就都如何聪明,懂得到用各样方法去侦察向她要好的男子的门
户与事业。还有另外一种女人,就都如何蠢笨,只晓得让一 个机会内的男子随意用热情攻
袭;结果则在征服下归了那她怕他还比爱他成分还多的男子。他,让人挑选既已决不会及
格,征服人又缺那无耻无畏的勇气,凭什么敢在对女人事上乐观?
“然而我有长处,这长处也将有女人需要这个,”他想着,又稍稍自慰了,“女人不
是一个样,也象鸭子不是一个样那样:不住溪不见过水的鸭子,也许不欢喜泅水,倒欢喜
上树。这哪里能断定这个女人不是一个特别性格的女人?”
他唯一的又很可怜的,是希望女人中也有特别的,而这特别的意义,又似乎是不要他
去爱,她也将来纠他缠他,撒赖定要同他要好。也许是有!也许他这时所遇的就是这样一
个女人!
命运安排中使这个无聊汉子要更多一点苦,这女人恰恰从后门夹了书去上学。听到门
开时,他把脸贴到窗上去,就见到这女人打下面弄堂过身。从窗中所见的女人,却不是全
体。
一件青色毛呢旗袍把身子裹得很紧,是一个圆圆的肩膀,一个蓬蓬松松的头,一张白
脸,一对小小的瘦长的脚干,两只黑色空花皮鞋。是一种具有羚羊的气质,胆小驯善快乐
的女人。是一个够得上给一个诗人做一些好诗来赞颂的女人。是一个能给他在另一时生许
多烦恼的那种女人。
他想在这个印象上找一点毛病出来,譬如说,年纪大,脸上有雀斑,或者胸部不成形,
或者臀部发育过火……想在这毛病上提出一点自尊心,却不能找出。从走路上,他想看出
这女人是个阿姨之类的女人来,好莫在心中太难过。可是这女人的俏处美处,却有一半是
在走路的脚步上。那么轻盈与活泼,那么匀称,都只给他更相反的一些希望。
这样一个好女人,住的地方去自己住处又只是那么一丈二尺远近,真是一具使灵魂也
不忒安宁的闹钟啊!
先是自伤着,这时却又睁大了眼睛,作起许多荒唐的梦来了。
他想到同这女人认识以后的一类事:他想到他将使这个女人如何搬家搬到一个好一点
的房子里去。他想到帮助这个女人,使她在念书中不受生活上压迫。他想到这个女人将来
可以同他在一起过生活,而这生活又是很充裕,一切满足的。
他又想到他将来会为这女人——那当然算是他的妻——写一 本长长的小说,大致超过
一切目下的长篇小说,从这小说上她成了一个不能老去的美丽漂亮人物,以后社会上许多
人都把他们生活拿来作谈话资料,他却便把这小说得来的一千块钱稿费为女人买顶精致的
画具,以及一个值四百块钱的提琴,女人自然就常常用这个提琴为他拉有名的外国曲子,
让他坐在大写字台边一旁写小说一旁听。……他且想到他那个时节两人来说当初相识的事。
“是的,我要问她第一次见我是怎样一种心情!要她说她怎么就爱上了我!那自然只抿了
口笑。然而一定要说。然而一定不说,只是笑。那笑的神气,就值得在颊的左边右边亲一
百次!”
他想到妻的笑着的神气,却在瘦瘦的颊上漾着枯涩的笑容。可怜的样子,在他心中不
但爱情温暖着的家庭已完成,他把小孩子也在最短一瞥中培养到五岁了。
……新学得吸烟,就把一支大炮台用小牙烟嘴吸着,小东西来了。去,爸爸要做事,
为去学阿丽丝游我们苗乡里时的故事啊!不肯去,则罚坐在桌边,为爸爸数稿子页数。…………
还应当有一个女儿,小洋囝囝那么爱娇,为小东西找一个妹妹!是的,哥哥五岁则妹妹三
岁,是这么才合式!
怎么样就同这女人好下来,他忘了。
三
他自己伤起心来了。无缘无故的,只伤心。心中酸着,辣着。他要哭。要揉打自己,
要嘲弄自己以后又来可怜自己。在一种已渐成了规则的浪荡生活上,忽然加上一件把心神
搅得无主的事情,这事情过细研究起来且正若是自讨自找,他为了俨若悭吝这荒唐梦境所
耗的精力,就在要求与牺牲上生出赔本的难过起来了。
是赔本的事。
就是那么单想,单恋,来在脑中结成若干崇楼杰阁,若干喜剧与悲剧,若干眼泪与缠
绵,以及一切有家室人有爱情人的痛苦与欢乐,把实际权且抛开。但眼睛一睁,当面站的
就是一个圆脐形的墨水瓶,墨水瓶,是这梦与墨水瓶,只是两个敌人。在势便难于两立。
做着梦下去,墨水瓶上便只合积上一层灰,墨水也只合慢慢起了沉淀,下月的用费便成问
题了。使墨水瓶能尽其天职,终日把那枝形同僵蛇的樱桃枝笔杆周旋于墨水瓶与白稿纸之
间,则这梦已破碎到成了小片小粒,——是这样,一面写着一点什么小说,一面让邻家一
些俨若含有恶意的软语轻歌摇撼着这不安定的灵魂,这又将成什么生活!
在损失上去计划,是这个人所不惜时间划算的。
在光明美满的梦中他发见了一种自己终不能忘了自己是在做梦的苦楚,这个使他自馁
下来,想找另一条路走。走另一条路,便是他应当学一个骑士(恋爱中原是有骑士风味一
类人者),学骑士,便是说他应卤莽一点,脸厚一点,怎么设法先试同与这女人接近。
也许是这样作去,这梦的基础就居然稳固了。也许这样作去是给他勇于自保的一种好
方法,前进既有了阻碍,则急流勇退不失其为明哲。
然而焕乎先生能成其为骑士或明哲不?全不能。
他想如此还不如死了吧。也不会真如此轻易死的。然而想。
“想到死”,凡是一为了类乎这种麻烦便要想到死,是成为生活上必需的一种思想了。
从死上,于是到怎样难受的创处。把手指按到腰或头的某一部分,被按这一部分便灼着烧
着。于是便俨然一具尸骸的陈列。于是第二天便有若干混账东西,装作朋友来为开追悼会,
或在报纸上做成若干追悼专号的文字,结果则好了一些曾花了些钱买有他小说集的市侩,……
就为了不能尽让这些人赚钱,便应好好活到世上了。好好活到世上啊,那为女人也就暂时
莫过分从好奇中来悲哀吧。
不过到另一阵儿,仍然就应得要从这可笑的思想上救出自己!
不死,那怎么来活,还“好好的”?结果是想还是想,悲哀也还是悲哀,到悲哀抵挡
不来,又想死,仍然也让它想。所以放心的是决不会因仅仅想到就能去做,想到不一定能
做。
“在笑”!这是与先一段思想距离一点钟以后的事。
就听到一种笑声。轻倩的,娇的,甜的,以及近于在谑戏中被谁拧着扭着挣扎不来的
纵声的笑。这笑声,影响及呆坐在桌子前的焕乎先生,比吃酒还容易醉。——不,这是说
比嗅着酒还无可奈何。当一个酒徒把一种好酒置在鼻下闻着时,感觉到要喝要咽的欲望
(至少是要抿一口),连抿一口也无从的嗅着,真是无可奈何!
这女人或者是从前面大门回的家,不然那走路声音,从衕子口到门前,是那么长长一
段,他总不会不知道。也许又是另外一个女人,因为这笑声的放纵竟似乎不应出于那女人。
即或是另外一个女人,这笑声也很可爱。
“不拘是谁一个的笑声,总之全是作孽!”他想着,“若我是一个女人,我就不乱笑,
因为我明白在随意一笑中,即或不是当面,所能给另一个男子的痛苦也就很大!”
然而笑者还自笑,不到一会且轻轻唱起歌来了。
一个年青男子的趣味,在女人的不拘某一事上总比在许多事业上还固执。焕乎先生就
是那么一个年青人。他把所应作的事全搁下不干,一个下午全在一种听隔壁戏中消磨了。
日子是这样消磨,与在一个电车上消磨究也无多大分别,不在此呆就跳上电车,让一
个车匣子把自己从静安寺搬到靶子公园,一趟至少将近花一点钟,来去既当加倍,则应在
两点钟左右了。花两点三点,到电车上坐着,去看一切人,与一切货物房子,并嗅一切女
人身上的香味,及一切男子的臭味,这已作过无数次,似乎也应换换方法了。如今则所换
的却近于意中所选择下来的一件事,不过假使是下文还能如意中所选择,那焕乎先生将成
另外一个人的。
这另外一个人,将把幸福与苦闷揉成一个生活,这生活是因来到这上海而得的一种事
业,事业的继续把自己就变成另一个人,……只有天知道这样一件事!
这生活,如果如所摹拟的继续的下去,那真是一个荒唐不经的梦了。在不拘谁一个人,
总能如所希冀去做吧。到焕乎先生,则将成为一个笑话同一件喜剧。他要的是生活,随到
生活后面的一切责任初初还不曾想到。譬如同一个女人玩一次的代价,至少是献殷勤花十
二天,用钱二十元,写信八 次,(也有本不必要的,但那是什么样的命!)他并不缺少空
闲,也有钱,可是这方法,真是一个“大举”!他会设什么方法使一个女人陪到他去上卡
尔登看一次卓别麟的马戏?他会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