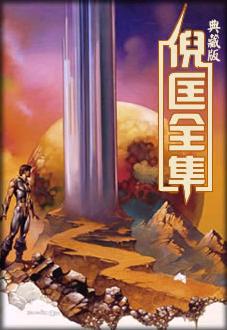在劫难逃 作者:万方-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怜的身体。乳汁将使鸟儿长出翅膀,乳汁将在高空飞翔。我想象出那样的梦境。与此同时,奶头在他花苞般的嘴里一阵火辣辣的钝疼。在我的怀抱之中,我们互相给予。
在我还小的时候,记得有那样一种沉寂无声的昏昏然而又十分悲凉的心境。我面对墙壁坐在一张椅子上,室内光线昏暗,赭红色的木窗占去了朝南的一面墙,但窗子都被布帘遮蔽着。屋外门廊上常有老鼠迅疾无声地溜过去。门口的廊檐上,一到天暖之后,马蜂就飞来了,一点点营造它们的窝巢,像莲蓬一样的东西,它们钻进钻出,密匝匝地围住自己的家。孩子并不特别地觉得害怕,只是有时进门会有点别扭,总感到身后有什么令人心跳的事在发生。但她从未想过把它们赶走,毁掉它们的窝。马蜂窝和这幢砖木结构的旧房子已融为一体。我是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面对墙壁坐在一张椅子上,马蜂在门廊上嗡嗡作响。孩子的身体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低垂着头。假如把那样的一个雕像起名为“受罚的女孩儿”是很合适的。确实,那孩子是在受罚,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要她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悔过。她知道父亲如果不是气狠了是不会如此的,所以她也就格外地乖。只是她不知道二十分钟到底有多长,这是她感到悲伤的一个原因。
屋子里的光线气氛使孩子昏昏然。熟捻的幽凉从屋的角落向她轻轻吹拂。在某一瞬间,她自觉听见一个声音,她没有回头,但她的心因欣喜而加快跳动。
门几乎不被觉察地推开,母亲出现在门口,她闪身进屋,然后立刻把门关上。孩子一动不动地坐着,感到屋子里的一切都变得神秘而有趣。她用耳朵去探测,用超出自身的力量管束住自己小小的头颅,不要向后转动。为此,一阵微微的颤栗从皮肤上飕过。
颤栗还未消失的时候,就有一只手放在了她肩上,像只小鹿那样,她飞快地扭过头,啊,到二十分钟了吗?母亲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全部内容。她轻轻地摇摇头,用手在女儿的后背抚拍着,好像为了掸掉灰尘。
母亲的面容有如晨曦中的湖水。
2
她听见一声叫喊,她们都听见了,是父亲在喊。母亲迅速地离开了她,房门被关上了。不,那时她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仇恨。当她听见父亲低哑的声音说,“你进去干什么!你为什么总要在这个时候去表现你的感情!”这时,她却已经体味到那种她永远也不想体验的情感。
父亲的话消失在寂静中。她无法想象紧闭的门那面的情形。剩下的时间漫长得没有尽头。直到父亲在外边叫她,“你可以出来了,”她也没有立刻站起来。
在父亲面前,母亲是另一个人,好像她不能和父亲同时爱我。我又听见了父亲的声音,有时他就当着我的面说。这孩子本来不是这样的,现在是母亲,是她让孩子反对他,她如愿了吧。他大声提醒她,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所做的一切是为孩子好,让她别忘了这一点,不要那么自私。他的声音里蕴育着雷闪,隆隆作响。至于那些话,可能并不十分准确。而真正记忆中的只是那突如其来的可怕的场面。
母亲脸色苍白,她的眼睛那么湿润,使孩子以为立刻会有泪水流出来。她害怕极了,她惧怕看见母亲的眼泪,胜过惧怕任何事物。仿佛隔着遥远的距离,她再次听见母亲说,对不起,我错了,你不要再生气了,我承认我做得不对,你看行吗?
刹那间卷起的风暴,又在刹那间归于沉寂。但是,孩子感到屈辱,她不愿意再呆在那儿,就走到外面的门廊上。鸟儿通灵的鸣啭,把她的注意力引向树梢。之后,她吐出一口气,比像她那样大的孩子的气息要深要长。这样的叹息,大人们是不会听见的。
要过很多年,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她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父亲和母亲都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爱着她。他们爱她之深之重是她无法探知的。因为她不仅仅是他们的孩子,她还是这两个人生活的锁链,是她,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忍受他们所不想忍受的一切。这是在漫长的夜里,我独自沉思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寻求而来的,它是一种呈现。在黑暗的寂静中,我看见了它,它慢慢地显现出来。母亲是不知道这些的,她无邪、充盈,连她的痛苦也那么圣洁。
她就是那个身上洒满繁花的女人。
那时候,我天天为儿子洗澡。洗过之后把他抱起来,裹在宽大的毛巾里,轻轻揉搓,日复一日,手中日渐沉重。在这期间,我的身心感到劳累与孤独。我把这感觉告诉了我丈夫,他说,人家都是这样,还能怎么办呢?我想说,办法很多,比如你晚上不要再出去玩了。可是我知道,如果我这样说了,他会开心地笑着,一口答应下来。之后依然如故。
我们已经不睡在一张床上,现在是儿子在我身边。睡觉之前,他常站在床头,俯视那个小小的占领者,有时还伸出手去逗弄他,一旦有了反应,他就会满足地笑出声。过一会儿,他的目光开始涣散,微笑地打个呵欠,叹息道:哦,真困死我了。他双眼迷蒙地走向自己的床,躺下之后,像儿子一样迅速地入睡。
黑暗的房间里有三个人的呼吸,可她仍感到孤单。她不知道还能企望什么,也从不去想以后的漫长的日子,不去想今天与昨天和明天的区别。脑子是空荡荡的,却异样地清醒。她躺在那里,日常生活的影子一点点地、慢慢地与旧日的影子重叠在一起。真的,有时她会把自己与母亲混淆了,这感觉使她微微一笑。她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平静地对自己说,那样的日于不是已经开始了。天哪,她忽然领悟到,这孩子,孩子是上天赐给母亲的救星!把她赐给了她的母亲。现在,这婴儿又在她身边。上天的赐予,不是吗?
她急切地伸出手臂把灯打开。
房间从黑暗中跳出来。在灯光的瀑布中,她涌向那张小脸。事实是,她按捺着自己,慢慢地凑近……。是的,它的魅力无与伦比,经久不衰。在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次的分离之后,都那样新奇,令人激动。
她面对着他,用胳膊支撑着头,长久地凝望。
这奇怪吗?这是深情,抑或一片爱心?
不,我时常感到这行为是属于大自然的,如同植物生长的一种状态:一株开放的渐渐变淡的花朵;被果实坠弯的那些枝条;它们不由谁的意志来决定,而是造化的无穷伟力。
这时候,妈妈,我无须再向自己解释什么,它安慰了我的过去,我的将来,也安慰了我的下一天,再下一天。
十分钟前,邻居来告诉我,你爱人来电话说他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说完冲我客气地笑了笑。我真该感谢她,而且我确实说了谢谢。谢谢。我又说了一遍。
还没有吃饭吗?在我身后,厨房的门静寂地洞开着。对,还没有。儿子呢,好吗?他在哭泣,可是我却说,好,挺好的。
我突然拉住她的手,把她拖进屋里,一脸绝望哀告的神情把她吓坏了。你会给孩子断奶吗?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吸吮奶嘴?如果我坚持下去,他会不会饿死?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呢?她充满了同情之心,同时又是个很有礼貌的女人,因此,她面带笑容,转身离去。没有答案,没有。我没有问,没有企求,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明白不会有转机了,不会有人出现来拯救我。我的期待是荒谬的。那天,风撕扯人心地尖叫,把城市刮成了旷野,房屋像是孤寂的洞穴。那天,我要给儿子断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再三地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我的行为激怒了他,他放声嚎啕。我空着肚子,心力交瘁,越来越多的汗粘住了内衣。
我在想,我最终是怎样治服了我的儿子的。是用开水浸软了奶嘴,还是把奶嘴放到锅里去煮,或是用一只胳膊抱着他,另一只手悬着奶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一个劲儿地对他说,宝贝,吃吧,吃一口吧。
不,不是这样,都不是。是他自己战胜了自己。
是他的欲望的得胜。我所指的不是饥饿,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欲望。他不再吃我的奶了。那坚硬的双乳分泌出的乳白色的汁液,已成为他的记忆。而他绝不为回忆困扰。他用一双小手捧住奶瓶,他的嘴有力地吸吮着,向天吹奏着一首无声的美妙无比的人生之歌。我心花怒放,不可救药地沉醉了。
女人,多么容易满足。好像曾在哪本书上读到这样的话。而我几乎没有时间看书了。是风掀开桌上的书页,灰尘也悄然飞来给它们以另一番装扮。但无论怎样,它们那深不可测的魅力在世间永驻。方正的、薄与厚的,破旧的、崭新的,令我眷恋的。在某一天,记不清的日子,我和它们分手。好长好长的分手啊。可是我却知道了这个事实,女人是容易满足的。
女人永远在期待着。
她们总是执迷不悟,不管岁月如何改变了容颜,她们的胸中永远隐藏着那些陷阱般的渴望。想想看,瞬间的注视,目光点燃了目光,抚摸的语言,仰面躺倒时那如坠深渊的旋晕;还有誓言,些微的赞美之词……
结局往往不期而至。
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看到了那铅灰色的、由远而近的阴影。我说过,这阴影和我幼年生活中的一些印象重叠在一起。透过窗上的玻璃,你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女人睡不着,来到丈夫床前,伸出手推推他的胳膊。他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别碰我。那痛苦的神情使她停住手。痛苦随即消失了,代之以和美的鼾声。那是健康者们令人向往的忘却一切的睡眠。她在床边坐下,向里挤了挤,费力地侧身躺倒,那姿势肯定有点儿可笑。这时候,睡梦中的身体顺从地向里移去,她可以平躺了。与此同时,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胸部。
她躺在那儿,承受着那只手臂的重量,在一片混沌之中,也可能她就这样睡着了。她梦见了自己。
一个腼腆的热情的小女孩儿。
是的,那个女孩儿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很安全。多么奇怪,在人所具有的无数感觉中,她紧紧抓住的是安全感。这感觉来自外界,来自她的双亲,来自母亲对她永不休止的亲吻和关注。母亲的吻无限温存,漫长得如同中止。就像是那张照片上的她们,母亲的嘴贴在她的脸颊上,照片并不很清晰,但完全可以看出那份醇厚的情爱。
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放在一个褐色的木镜框里,而镜框现在已放在了抽屉的深处。记不清是由于什么契机把它收起来的。也许因为玻璃是易碎的,也许在哪一天,她忽然发现镜框落满了尘土。抽屉几乎不用开启,它在书桌的最底层。幽暗、宁静。在那里,许许多多飘流的记忆被固定成一个形象,使怀念的人放心,相信那将永远不会忘却。多年以后,十几年,几十年,衰老格皱的手会翻出一些被当作纪念的物品。但,也许,生命会在这之前完结。
女孩儿和她的父亲却没有这样的照片,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如此亲热。父亲也亲她。父亲的亲吻在她的记忆里反而更为鲜明具体。那不好闻但却吸引她的气味,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吓与兴奋;她可以抱怨父亲,可以使劲推开他,从中获得权威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