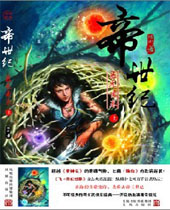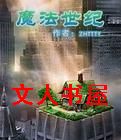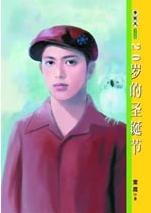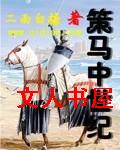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先说我母亲。我父、母都是日本留学生,母亲先学医,以后又攻读工艺美术。父亲挺封建,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徒有一肚子才学,却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我的命运自然比母亲好些,可也没少磕磕碰碰。我还只有四岁时,母亲就要我去读书,她对我学业很关心。渐渐大了我才明白,母亲是把自己失去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这个女儿身上……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大部分学生是教会中学保送去的,又多是贵族子弟,一门子心思几乎都耗在吃穿享乐上。学校里三天两头开舞会、茶会,女士们男士们竞相比着气派和时髦。上课、下课都说英语,似乎谁都以为自己真成了个黑头发、黑眼睛的英国人……我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也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读了不到一年,便退学了,以后报考进了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
我总觉得一个女人该和男人们一样,先得有文化,然后得为我们这个日渐衰落的古老民族做些什么。但结婚后我没有工作,一直坐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不甘心呐。我便读英文小说,翻译罗素、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关于人生观方面的论述,头几篇登在《大公报》上。还学了点德文,又学写过散文。次年,我便找到了工作。1947年,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给亚非国家学生资助奖学金赴美留学一年,在中国委托美国新闻处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十个城市招考。当时,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三十七岁了,家里又是这种境况,但我还是去报考了。结果录取了两名,一名是上海沪江大学一个搞原子能的,北平的这一名就是我。一年后,我先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英国文学系上了一段,以后又到哥伦比亚教育学院英语教学专业学习,并获得了英语教学硕士学位。于是这辈子与英文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后一直在新华社对外部,无论当记者,当编辑,用的都是英文……
我女儿采采,“文革”前的老初三,1968年去了北大荒,做了三年农工,又当了一年半的卫生员。她父亲去世后,组织上照顾我,1972年底调她回北京,分配去北京焦化厂当工人,跟着一位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女同志搞化验,跟了一年,色谱仪等精密仪器就能独自用了。这时,厂里推荐了十五个人考工农兵学员,录取了八名,她的成绩比这些人都好,却被甩下了,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关于我去美国留学一年的事,“三反”时就调查过,证明了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文革”中又翻出来了,大会问,小会追,我成了“特嫌”。虽然材料一直拿不出,影响却像一条影子一直拖在身后,这不,采采的前程又一次被耽误了!我这当母亲的自然伤心,想不到女人在旧社会想读点书难,在新社会又这么难,而且阻力还不是仅来自封建思想,还来自那翻云覆雨,叫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采采这孩子也伤心,但不颓废,学习上一直抓得很紧,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她一考就中了,专业对口,录取在北京化工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学了四年,又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分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所属的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作。
采采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学的东西又很有用,主要研究何种化学物质能致癌,我就希望她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隔行如隔山,她搞的那一行我不懂,帮不了她任何忙,我就在经济上支持她。她一家人住在我这里,两口子工资只有二百来元,两个小孩,请了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就得六十元,再加上吃饭,一个月得一百多元。还剩下一百元左右,你说这怎对付四口人?物价还铁了心在涨,它才不管你中年知识分子可怜不可怜。再省不能省孩子嘴里的,可省大人碗里的,俩口子又正当盛年,采采是站里的业务骨干,她丈夫正在铁道科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亏了身体,惹出病来,还不得又成个张广厚?我可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好在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我可以帮忙来落实。我的退休工资,加上我的大部分译稿费,都交给了采采。这样,我辛苦一点,全家人的生活可以好一些,采采俩口子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也挺充实……
我还在精神上鼓励采采。是我要她报考“GRE”和“托福”,争取出国的。这不是赶什么时髦,尽管我很少出大门,可出国热我还是感觉到了。在我们这新华社家属大院,男同志不说了,女同志也出去不少,年纪大的有三十几岁的,还有离了婚的,出去了就一般不想回来……我纳闷:美国生活是富裕,可那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即使入了籍,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油和水能真正溶为一体吗?除非你是杨振宁、李政道,除非你是“电脑大王”王安,人家对你不怎么看得起。人家的智慧,人家的汗水,二百多年来沐风浴雨创造出来的天下,如今你丢下仍贫困落后、急待振兴、富强的祖国,跑到大洋彼岸去分享,你自己心里也有愧呀!可是国内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似乎非要拿根棍子将人才赶走不可。
关于采采,我是这样想的:论文凭,她已经有硕士学位了;论工作,还顺心,单位对她也重视,去了两年,送她去读了五个月的日语强化班,有什么口译、笔译任务都派给她做,还花了十万元,买了台美国原件、国内组装的色谱仪,交给她负责;论家庭生活,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得盯紧她的功课,小的只有两岁半,正是满处疯跑的年龄。我也七十了,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自然我也希望能有女儿在身边照应……采采并不是非出去不可。但她一直很关注国外与自己相同领域的科研动态;外语又的确不错,今年她站里来了位美国化学家,开办新技术讲座,由她担任翻译,从头至尾都拿了下来。有这样的兴趣,又有这样的条件,出去一趟开开眼界,学习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回来,对提高她的研究水准大为有益。亲友们也都认为她不出去一趟,早晚会后悔。得承认,也有点个人打算:再怎么说,我也是风蚀残年的人了,能再在经济上支持女儿一家几年?我感到在采采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两个太大的差距:一是他们的贡献与他们的报酬差距太大,二是他们的收入水准与部分体力劳动者的差距太大。前几年报纸上就在喊: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抵不了一个保姆,现在还不是照样,看来三年五载还得如此。采采出去一趟,她丈夫也准备出去读博士生,总能攒些钱,将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一下……
采采出去时间长了放心不下家,同时对国内的情况又不熟悉了。她不会去个三年、四年,也不会同丈夫一道出去,而是两口子轮流出去。俩人也都说:“我们是第三世界,学了东西就回来。真要去第一世界当个三等公民,那太没意思了!”
说起来也有意思,我是三十七岁出国留学的,采采则是三十七岁决定出国留学的。晚都晚了些,而且又都是非个人的原因造成的。但历史毕竟是进步了,国家毕竟是开放了,要不然,一个“特嫌”的女儿,哪敢再去美国?采采学成回国后会有一番成就的。我想,我九泉之下的母亲将会为她的外孙女感到欣慰……
三
考“托福”,英语需达到相当水平。“托福”考试要求相当严格且程序安排也是相当周密的,试题由美国方面直接拟定,试卷也收拢回美国直接评判。高校里的学生好说,英语课、英语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社会上有志于此的人们却没有这番“月色”,于是又一种特殊行业应运而生,名称形形色色——
新概念英语班;许国津英语班;高级口语班;基础英语班;出国留学人员英语训练班;《美国之音》中级美国英语班……从全国各大都会曲曲折折的大街小巷里,从一所所中、小学里冒了出来。翻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时不时能见到此类补习班的招生广告。
在北京,学习期限由两个月至半年不等,收费三十元左右。外国人教的有一所,即民办的光华外语学校,期限四个月,收费四十元,该校设有八个班,学员达三、四百人。各校教学质量有高有低,学员们却绝对地虔诚,竖起双耳生怕漏了一个字。每个星期两个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三伏寒冬,一下班,多数人空着肚子,径直奔向各个教学点。等拖着条近似死鱼的身子回到家里,远的要过十点,近的也是九点左右,胡乱塞上几口后,书包里、案头上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做,一盘盘磁带要听。学员们同窗苦读一场,却忙得彼此之间叫不出姓名,更不能深交,只是在匆匆交臂中,彼此投上一个疲倦而又会心的微笑……
从出国留学生身上获了利的,不仅有非法的外币倒爷们,和合法的形形色色的英语补习班。连香港的某些机构也红了眼,急切地插上一杠子。
对数万计的自费留学生来说,去美国是第一选择。然而,近年来美国学校挑选海外学生的标准越来越严格,除了一小部分“托福”考试在600分以上(个别院校要求550分以上)、英语成绩特异者,有幸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外,多数人即使被美国高等院校录取,也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在美国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才能获得签证。于是,不少人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其他英语国家……
1986年下半年起,在广州传出一则新闻,宛如彭丽媛的歌喉般动人:只要交纳一笔报名费,不论英语成绩如何,也无须经济担保,便可到澳大利亚各大学、院校学习。这只“歌曲”的精彩部分是:因为澳洲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该国政府将在1988年建国二百周年大庆之际,大赦违反移民法的人,届时留学生凡有此愿望的,都可变成澳洲的永久性公民。
不知是香港的某些机构从中嗅出了什么门道,还是这则新闻本身就是由它们炮制并进口来的,一时间,纷纷开设为大陆同胞联系留学澳洲的业务,从中收取数量可观的手续费,而且这手续费还拒收人民币,只收港币。其中一家名为Aeademie Asia的辅导留学中心,曾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题为《自费留学英国、澳洲的佳音》的广告,内称该机构将邀请英、澳著名教授,于1987年5月间赴北京、上海、广州访问座谈,解答自费留学的有关问题,届时将有专人洽商具体出国事宜……
自费留学者的大海上,赴美国的大浪未见衰退,赴澳洲的狂潮又在迭起!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一下注意到了:昔日门可罗雀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今日也蒙受着“倾盆大雨”……
签证处官员霍尔姆斯告诉记者说:“申请签证的留学生人数突然激增,结果迫使大使馆小小的留学生签证处从澳大利亚请来临时工加班。同时,有几个星期申请表格供不应求,不得不赶去香港加印。事情变得一团糟,我们被人潮所淹没。工作人员受到不顾一切的学生们的打扰,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或尾随我们到家中拜访。有一个人为了给一位亲属办签证而谎称同我约好了见面时间,结果混进了签证处……也许他们习惯了走后门,可澳大利亚使馆没有后门可走。谁打扰使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