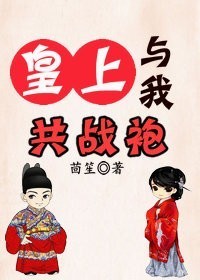血族与我-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麽时候徵用。没有法律、没有审判,任何不幸的意外都没有申诉机会…只有刽子
手等着我们。」他顿了一下,端详着我的神情,「二十一世纪了,女士。你认为
这是应该存在的吗?」
我没露出任何神情。这是个言语上的陷阱,我不会上当的。
但他用中文又问了一次。
「…我猜,神父。你要我问何谓『不幸的意外』,是吗?」我对他笑了笑,「然
後设法激怒我…再用更有力的论调让我信服,对吗?」
他的神情出现了一丝变化。
当你跟一个聪明的施虐者生活过,就很容易推论出来。这是种老把戏。我想他调
查过我的背景,我的确对被虐这样的事情非常容易动怒。但我也了解这些聪明的
家伙,精细而残暴。
如此迂回的将我引入这个陷阱之中,令人几乎察觉不到的压力。但他们是猎食动
物,施虐者。怎麽样隐藏也还有那种聪明却疯狂的气息。
在他彻底被我激怒之前,我将语调放得很平静,「你直接说好了,神父。让我们
明快的解决这件事情。你们要什麽,和可以给我什麽?」
「…你和兰非常不相同。」他的语气有些失望。
「我缺乏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精神。」我对他微笑。「我被你们绑架过,记得
吗?」
一声深沈的咆哮让我下意识的抱住脑袋,但没扑到我身上。神父单手掐住一个女
吸血鬼的咽喉,毫不费力的将她举起来。「黛比,冷静点。」将她远远的摔开。
那个叫黛比的女吸血鬼没有冲过来,却远远的叫骂,「巴尔该杀了那个婊子!留
她一命,结果还不是被罗斯杀了?凶手!」
「黛比,出去。」神父冷冷的说,「去上帝面前忏悔。」
我倒没想到她会乖乖的走出去。看起来,神父的地位很高,不然就是活得很久或
权势很大。
「…很抱歉给你不好的印象。」神父真挚的看着我,「但第一印象都是不准的。
」
我勉强笑了笑。「…我们别迂回,直接了当的谈交易吧。」
「…我需要血族的身边有一个人,让我们避开被伤害。」他递了一个很小的东西
给我。大概是窃听器之类的吧,我想。他後来的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你甚至
不用开口说话,只要放在你的皮包里。」
「那我可以得到什麽?」不是我真的需要什麽,我不需要过多的钱,我已经够用
了。但我若不显得贪婪,就不能让他们放下戒心,好把我放出去。
「永恒的青春。」他平静的说。
我应该是不太会演戏,所以只能垂下眼帘掩饰。「…你不会伤害任何人吧?」没
我想像的困难,反正就当作我在想剧情好了。
「我保证。」
但他应该没被我唬过去,却把我送出教堂,并且在教堂外握了我的手。
这不是件好事。
我想过要不要把窃听器扔了,但决定还是留在包包里。我仔细想过前因後果。他
提议把我摆在一个「间谍」的位置上,但这种手法真的很粗糙。简直有点欠考虑
。
他知道我的存在,而且是个行走在阳光下的吸血鬼。说不定就是他派出入侵者试
图绑架我的…绑架我的目的?
就血族的眼光来说,罗斯是有病的。他似乎很厉害…即使是血族的标准。但他有
相同或类似的「弱点」。
绑架我的後果,我想吸血鬼都知道了。罗斯发狂起来真的是超可怕的…所以神父
连根寒毛都没碰我。
等等。他知道我的存在,应该是因为罗斯带我去夜店见他的朋友们。所以说,血
族相关人士当中应该有他们的内应。但血族不太可能放着这个权势颇大的神父不
管吧?所以说…?
我得赶紧回家。
但我搭乘的计程车半路上被警察拦下来。警察颇耐人寻味的对我笑笑,「你被通
缉了,小姐。」
在众目睽睽中,我被押上警车,却不是押往纽约市警察局。我的坏预感居然成真
。
下午四点多钟,亚伯居然醒着。他从我包包里掏出窃听器,一言不发轻搓指头,
成了粉末。
「或许你该等罗斯来。」我摊手,用英文跟他说,「没想到你还醒着。」
「嗯…这几年我都设法『调整时差』。白天总要有人醒着。」他斯文的微笑,对
我说中文,「林小姐,你的英文发音非常不标准。」
「听得懂就好啦。」我也换成中文。「你要怎麽处置我呢?」
「杀了你可能比较好。」他温和的说。
「然後罗斯抓狂,血族之间反目成仇。」按耐住恐惧,我理智的谈判。
「纽约每天都失踪许多人口。」他含蓄的威胁。
肯谈到这地步,情形可能不会太糟。「然後罗斯抓狂的翻遍整个纽约?你们不想
发生这种引人注目的不幸事件吧?」
「你怎麽知道他肯为你这麽做?」
「你又怎麽知道他不肯为我这麽做?你比我了解罗斯。」
对峙了一会儿,他轻笑,「聪明的女孩。可惜太野心勃勃。或许等罗斯来比较好
…」他冷冷的追加一句,「我有你跟叛乱者交谈的录音。罗斯可能想亲手处置你
。」
「好的。」我对他笑,「我想这样比较好。」
他没有对我严刑拷打或者扔到水牢。他把我送去他的「小姐们」那儿。
亚伯在纽约市郊拥有很大的豪宅,围墙内不只是一栋建筑而已。
我被引到侧栋,围着游泳池和温室,是个呈「回」字形的四层楼建筑物。出入需
要磁卡,挂在墙上的画和摆设,显得非常舒适。
我才被押进来,就有几位小姐迎上来了。总共七个,有的还穿着泳装,或飘逸的
落地洋装。
她们都是…Big girl。
我比较喜欢这种说法,而不想用「胖女孩」、「肥女人」。虽然她们的确尺寸惊
人…但我也不是什麽瘦子,难免物伤其类。
或许是眼前的景象让我非常震惊,因为我想破脑袋也没想过亚伯的「小姐们」其
实不怎麽小,甚至我不懂对我非常嫌弃的亚伯为什麽会有这些「小姐们」。一受
惊吓,我原本不灵光的英文就整个打结。
一个长得像北京狗的和善女士走过来,大约有两个我那样的尺寸。「欢迎,林小
姐。亚伯要我好好招待你。」她友善的和我握握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中
文,还去北平念了两年书。」
她叫做佩姬,很健谈,招呼我到新的房间。亚伯把我送到这儿监管起来,却没打
算告知这些「小姐们」什麽。所以她什麽都不知道,以为我是别个血族的「小姐
」,因为主人出国旅行或远游,暂时送来住几天。
「…主人?」我觉得脑袋都变成糨糊了,「佩姬,你念过哥伦比亚大学…」
「我拿到博士学位。」她有趣的看我,「你还没习惯吗?你的主人是谁?」
我瞪着她,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没有主人。罗斯是跟我住在一起,但是…
」
「是罗斯?浪子罗斯?」她啧啧出声,「我敢打赌你很受宠。你的漂亮姊妹也来
了吗?」
「没有那种东西。」为什麽她可以说得这麽理所当然?「只有我和罗斯同住。」
她神情凝重起来,看了看我的脖子,又拉起我的手臂,看着上面的咬痕。「罗斯
只有你?不可能吧?」
「请你不要说得这麽若无其事!」我突然有点发火了,「为什麽…亚伯胁迫你们
?」
「…林小姐,你是不是误会什麽?」她疑惑的笑,「你觉得我们是女奴?喔…哈
哈哈…不,完全不是。」
佩姬说,她和亚伯是在一场学术研讨会认识的,相谈甚欢。之後亚伯跟她约了几
次会,一个月後,跟她坦承自己是血族,不能专一的爱她一个人,却问她要不要
跟他走。
「…你就这麽跟他走?」我真的是震惊到无可复加。
她不大却清亮的眼睛柔和的看着我。「对。他并不是欺骗我,也不是对我施展什
麽魔力或催眠术。他的确不能如血族一样爱我,但他每周有一个晚上只属於我,
不只是来『吃饭』而已,而是他除了这堆肥肉,还看得到我的灵魂。
「你相信吗?我去婚友社联谊,又老又粗糙,连拼音都拼错的男人,还嫌我是头
猪。但亚伯尊重我、爱我,待我像是对待皇后。」
她用接近虔诚的态度说,「我愿意为他死。」
我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前厅环绕着他的是一群美丽的少女。」
「他是贵族,需要面子上的美丽。」佩姬耸肩,「但亚伯能跟她们谈什麽?指甲
油还是唇膏?她们只是另一群漂亮的姊妹。」
…血族庞大的後宫。悦目的是一群,赏心又足以「摄食」的是另一群。难怪罗斯
会说他讨厌亚伯这样养「家畜」。
罗斯太像人类了。
我心底动了动,看了看表,快七点了。一种强烈的心神不宁猛袭上来。
罗斯摄食我的血液已经很久了,有的时候,我会很自然而然的知道他醒了,或者
我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能第一时间找到我。日复一日,这种下意识的联
系越来越深。
他找来了。而且是燃烧着烈火般的狂怒。
「离我远一点,佩姬。」我转身跑出长廊。
「林小姐!」她追了出来。
「不!别过来,我不是要逃…」我紧张的尖叫,「别在我身边,他要来了!」
我刚跑到泳池畔,像是挨了什麽炸弹,一整个墙被打穿了,小姐们尖叫,烟雾弥
漫。
他连费神找一下大门都不要,这家伙。
罗斯拍了拍肩膀,笔直的走过来,抓着我的肩膀,「…兰。」
明明知道可能会这样,我却无法解释的红了眼眶。终究我还是替身而已。
「罗斯。」我尽量平静的说,「你打坏亚伯的墙了。」
他原本狂燃的怒火和惊恐,渐渐熄灭,眼神才有焦距。我想他醒来时没找到我,
就饿着肚子找来,根本就还不太清醒。
「你怎麽会在这儿?」他的眼神很迷惘,又转愤怒,「亚伯抓你来?为什麽?亚
伯!」
不知道什麽时候亚伯也出现了,他们搞不好真的会瞬间移动。
但罗斯往前一步的时候,亚伯那些胖女孩都纷纷挡在前面。目睹这一幕,我却有
种锥心刺骨的痛苦。
兔死狐悲。
「罗斯。」亚伯很冷静的扔了一个录音笔给罗斯。「我建议你带着你的女孩…去
弄清楚整件事情。你可以先用佩姬的房间…本来要给你用的那间似乎有些损坏。
」
他扯着我,有些茫然的进了房间,打开录音笔。听了好几次,才失去焦距的抬头
,虎牙已经伸出来了。
除了饥饿以外,我想他也是非常愤怒吧?
「永恒的青春?你也想成为吸血鬼?」他的眼睛几乎都褪成银色,虎牙伸得更长
,「你知道由血族转化的吸血鬼更接近、更强而有力?」
瞥见桌子上的一枝笔,我拿起来,抵住颈动脉。「罗斯,我不是兰。我不要当吸
血鬼。」
真是讽刺啊,真的是。我一直没有勇气自杀,现在似乎找到勇气了。「我也讨厌
乾燥花。」
我应该选钢笔的,浪费我的勇气。钢珠笔用了这麽大的力气,还是刺进几公分就
遇到阻碍,这一点阻碍的时间就够罗斯阻止我了。
他的吼声几乎吼聋了我,我猜喷出来的血也严重刺激了非常饥饿的他吧?我还以
为他会咬断我脖子哩,也的确吸食了太多血液。
「…我不要当吸血鬼。别剥夺我最後的尊严。」我沙哑的说,全身都很倦,大约
是失血过度。
「你不会。」他抵着我的额,一遍遍的叫我的名字,「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