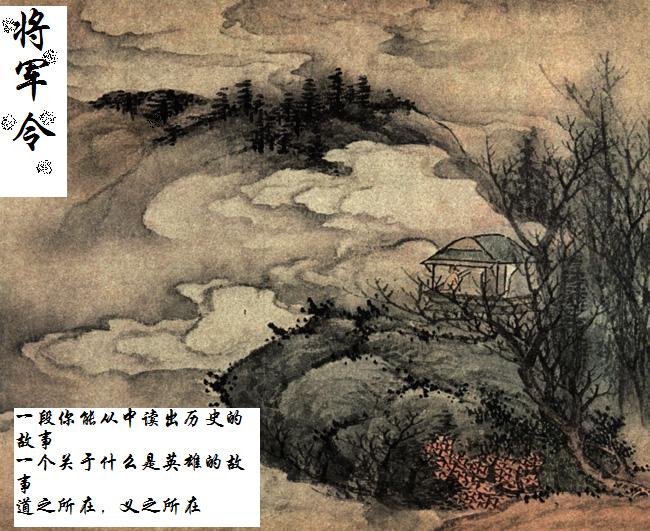将军要和亲-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她……是她害死了凤家九十多条人命,她用力地咬着唇,眼泪哗啦啦地流。
恨了十五年,怨了十五年,原来到头来,罪魁祸首是自己,她哈哈大笑,笑完了又哭,哭完了又笑,眼泪模糊了双眼,在眼前隔出一个空间。听不见雨声,听不见风声,一个人缩在一片血红的世界里,十五年前刑场上的一幕幕,不断地在眼前重复再重复。
刑场上,绑着凤家九十多人,郐子手刀起刀落,一刀一颗人头,滚了一地。四处是血红一片,血腥味从她的记忆里漫出来,一寸一寸地慢慢地漫过她的意识。
“红临。”收到九王爷送信赶到的遥隔眉锁得紧紧地看着在角落里的人,在她面前,蹲下来,撑着的伞递过去,替她遮去落下的雨,一颗心揪得紧紧的。
哪里来的声音?她像没有灵魂的布偶,眨了眨眼,抬头看一眼来人,又缩了回去。
遥隔
王爷真阴险
伸出手去替她拨开额前因雨水而垂下的头发,却触到一片冰冷的脸颊,忧心让他的眉狠狠地打个结,宽大的手掌顺着抚上她的脸,目光定在她脸上,细细地看,慢慢地说,“红临,知道我是谁么?”
凤红临抬头看了一眼,迅速地收回目光,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犹豫的回答狠狠地敲在他心上,像是有人在抽空他胸腔里的空气般。遥隔看着她,心一下子空起来,伸手揽过她,把脸靠在她发边摩梭,唇边扬起一抹苦笑。他一直以为,她把自己放到了心上,结果是,她真的把他记进心里,却没记到最深处。
这个时候,他叫不醒她。
“红临,是我,遥隔,记得吗?”他不甘愿,难平心头抑郁,再问一次。
怀中的人喃喃地跟着重复一次,又摇了摇头。
他嘴角泛过一丝苦涩,是自己不肯认输还是太贪心,想要在她心底最深的地方有个位置,到现在才知道,是他自恃过高。他又苦笑,扔了伞伸手要抱她。
她往角落里缩了缩,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人,黝黑的眸子里像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
“是我,遥隔。”左胸有痛楚浮出,遥隔握了握拳,又松开,伸过手去,不顾她的退缩,用力地将她拥进怀里,唇边勾起一抹淡笑,藏去思绪,在她耳边喃语,“是我,红临,是我,遥隔。”
“遥隔。”她在他怀里喃喃地重复一遍,声音缥缈得像从天边飘来。
“遥隔……遥隔……”仿佛硬要她记住似的,他靠在她耳边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名字。
“遥隔。”她跟着他说,像新生儿般,慢慢地,语气很轻,伸出手摸索着,最后抚上他的脸。
遥隔搂紧她,脸颊在她的小掌中摩梭,点着头低语,“对,是我。”
她的眼里找回一些焦距,像抓到浮木般,眼泪扑簌簌地掉不停,手慌张地抓上他的胸膛,紧紧地抓着他的衣裳,怎么也不肯放,半晌后才道,“是我杀了凤家九十多条人命。”
“不
王爷真阴险
是。”遥隔抚着她的头发,在她耳边坚定地反驳。当年的血案,只是迫不得已,不能怪任何人。
“是我!”她突然哭出声,手指抓得泛白,指甲几乎要陷进他肉里,说得重重地,“是我杀了凤家九十多条人命。”
“不是你,不是。”遥隔在她耳边不断地重复,伸手去掰她的手指,让它们松开来,放在掌心轻揉,然后抱着她站起来,将她的头按向自己的胸膛,好重好重地叹气。凤红临是性情中人,爱恨都写在眼里,这些年来,花为媒教她不能恨,不要恨,为了就是这个么,她失控。
一只油纸伞遮过他们的头顶。
遥隔抬头看打伞的人,打算道谢。
九王爷正耸着肩,微笑地看他们。
“为什么告诉她?”看清来人后,遥隔半眯着眼睛,危险地盯眼前的人。
“该知道的事,还要分早晚么?”九王爷邪笑着反问,继而又补了一句,“难道遥大人以为由你告诉她,会更好些?”
遥隔闭了闭眼,不发一语地从九王爷身边走过。
“遥大人,可别忘记与本王约定的事。”九王爷在身后轻道,语气平静。
“本官不会忘。”遥隔的身影僵了僵,并没有转过身来。
“那就好。”九王爷看着眼前背对着自己的背影又笑,笑完了叹息一句,“遥大人应该很清楚本王的作风。”
遥隔点头,抱着怀中人的离开。
第十章
遥府上下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侍卫们只着了寻常衣裳,依旧能从他们森冷脸上探出些眉目。
遥府今日,来了个不寻常的人物。
尽管如此,亦丝毫不影响雨后的景色。下了一夜的雨后,空气闻起来格外清新,风景实在是好。阳光从叶间一片一片的钻出来,四处都亮闪闪的一片,叶子是发光的,粗糙的树干一样泛着油的光泽,湖中的水波也是发亮的,随着风轻轻起舞,
婢女们在靠湖的一间厢房匆忙来回,许久之后,御医松了口气从房内退了出来,只余
王爷真阴险
下几个婢女在旁侍候。
厢房内的床边,坐了一名面色红润,惋若透着贵气的素衣妇人,伸出手去,一面抚着床上睡得极不安稳的人的脸颊,一面叹气,半晌后伸出手,一旁的婢女立刻伸手掺她站起身来。
“这丫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素衣妇人扬起一抹慈爱的笑容,看了一眼床上的人,才将目光放至一旁拧眉的遥隔身上。
遥隔上前一步要行礼,却被她拦了下来,只好抱了抱拳,“娘娘这不是要折煞下官。“
“罢了。”被称作娘娘的素衣妇人摆了摆手,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下,有些忧心地问道,“把十五年前的事告诉她了?”
“嗯。”遥隔点点头,刚才御医来过,她只是一时混乱,多睡些时辰就会没事。他忧心的是,九王爷是以哪种方式告诉她十五年前的事。
那人――为了自己喜爱的事,可以不择手段的。
“我不知道,会伤她这么深。”素衣妇人闭了闭眼,回忆当年。那年的情景,她唯一想到的就是保住女儿的命,甚至没问凤王爷把红临交给了谁带走。这十五年来,也不敢去寻她的下落,守着心中的秘密,一直到几日前,遥隔给她送了信来,说了事情来由。
她终于找到失散了十五年的女儿,却不知道,会伤她这么深,深得她不敢轻易认她,上天果然是公平的,九十多条人命,终归有要还的一天。
既然要还,都归到她身上吧,看了一眼床上连睡觉都难以安稳的人,素衣妇人叹息一声,脸上光华退去,仿佛突然老了许多岁。
“娘娘……”遥隔为难地看她,想劝却找不出话来,他说什么,大概都没用。
“是我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该还的,都要还的。”素衣妇人喃喃道。
床上的人动了动,像是要醒过来。
素衣妇人跨了两步想上前,脚步顿了顿又退回去。
遥隔立刻步到床边,望着床上的人,一动也不动。
睡了多久,她不太清楚,脑子是钝的,意识
不眨眼的女人
有些模糊,微弱的光飘进眼里的时候,她昏昏沉沉地睁开眼,手下下意识地摸索寻找熟悉的人。
“感觉怎么样?”遥隔上前握她的手在掌心,眼着闪着焦灼。
她摇摇头,眼光四处探了探,停在一处定住,瞳孔越睁越大。即使换了岁月,换了衣裳,她永远记得这双眼。在刑场上,笑得森冷又绝决,杀人的时候,不留半点慈悲。她手中握了几枚银针,瞬间起身,跳一床,朝那名妇人奔去。
遥隔紧紧地攥住她,用力地拥她入怀,紧紧地锁住,在她耳边轻语,“红临,她是你娘。”
“她不是!”凤红临侧过脸去,大声反驳,凌厉地目光扫他一眼,握紧手中的银针。
素衣妇人胸色惨白踉跄地退了一步,露出无奈的落泊表情,跌坐在身后的椅子上。她要尝到苦果了么,为十五年前那场血案付出代价。
亲生女儿要杀她,不愿认她!
“她是。”遥隔语气平稳,说得坚定,怕她没听到似的,重复道,“你知道的对不对,她是你娘。”
“我娘死在十五年前的刑场上,而这个女人,是刽子手。”她用力地挣开遥隔,毫不客气地朝素衣妇人横去一根手指,恼怒地瞪着她。一会后转过脸来看遥隔,讥讽地笑道,“你居然告诉我,这个女人是我娘?”
“红临。”遥隔脸色有些微恙地看着她,不知该如何劝她。
她吸口气,摇摇头,又点头,故作镇定道,“你告诉我,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是我娘?”
语毕,嘲讽地笑,笑完了,逼近素衣妇人,一双眼在她身上打量,声音森冷,丝毫没有温度地自顾说下去,“遥宰相,你说的是哪国的笑话?”
“红临。”遥隔皱了皱眉,上前一步要拉她。
她闪避了一下,退到一步,让遥隔的手扑了个空。
遥隔看着她,心里有隐隐的难受,明明是母女,却相逢似仇家,凤氏皇朝这个王位,到底要捉弄多少人?
她闭了闭眼,睁开,对他脸上有些微
你没资格喊我的名字
僵的表情视而不见,扬起一抹熟悉的笑容,眉弯弯,眼弯弯,仿佛不曾发生过任何事般,说得讽刺,“果然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遥隔只是拧眉,不说话。
“红――”素衣妇人想要表达些什么似地开口。
“你没资格喊我的名字!”凤红临转过脸去狠狠地截掉素衣妇人的话,微眯起眼,盯着她,尖锐地笑,“你大概没想到,三岁的我站在刑场外,看着你杀了一个又一个凤家人吧?”
素衣妇人脸色刹间惨白,一时站不稳,退了几步,险些跌倒。
她冷笑一声逼近,半点不饶人,“怎么,十五年后才来后悔,是不是太晚了?”
“我……”素衣妇人张了张发白的唇,似乎想要说些什么,看到凤红临眼里的森冷后,微仰头,眼角泛着湿润,闭上唇,没有说出口。她知道自己在十五年前,刀起刀落的那一刻得起,就注定要失去这个女儿。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自己有眼睛看!”她又抢白,冷笑道,“一刀一条人命,不知道你这些年是不是睡得安稳?”
“红临!”遥隔有些恼怒地上前,扯过她用力地将她压向怀里,“你这是何苦?”
伤人又伤己,手覆上她的,遥隔定定地看那紧握的拳,“伤人又伤己。”
她冷着眼看他一眼,想挣开,手却被握得死紧,只好放弃,脸上的表情却有些古怪,慢悠悠地像是要说给自己听,“谁说我伤己了?不过一个陌生人,还伤不到我。”
她笑,原本和气的脸上开始有些狰狞,咬着牙关,残忍地补一句,“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遥大人以为――能伤到我么?”
除了王位,她终于,不再拥有任何东西了么?素衣妇人满脸苍白,跌跌撞撞退了几步,摔进身后的椅子里,手抓着椅子,可以看到上面浮起的青筋,眼泪扑籁簌地掉不停。
“红临……”遥隔叹息一声,怜惜地看着她。知道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在父母呵护下长大,思想、身体都是
决择
没有伤痕的。他也知道,身心受过伤的人,哪怕是一些小事,都足以勾起众多伤心的往事。
“不用拿那种悲悯的目光看我。”她冷冷地看遥隔一眼,十五年前刑场上的回忆,一点点拼凑起来,渐成一幅完成的画面,想起来便彻骨的痛。
十五年关,刑场上,凤家九十多条人命,一个接一个,人头落地。
而当时的她,只是个三岁的孩子。
什么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