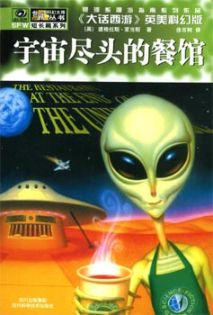偶人馆-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书导读
从飞龙想一踏入被称为“偶人馆”的祖产开始,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父亲生前的诅咒一样。父亲所做的模特儿,以各种诡异的形态,对自己进行无言的控诉。这些貌似母亲的模特儿们到底想告诉自己什么?而父亲上吊的那裸樱花树、每夜由房子某处传来的声音、连续发生的儿童命案、不断寄来的匿名信……这一切都使想一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
本书玄奇诡异,充分发挥“心理悬疑推理“的极致,甫发行旋即引起轰动,是一部令人难以抗拒的超级斗智推理小说!
主要出场人物
飞龙想一 我,画家(34岁)
飞龙高洋 想一的父亲,已故。
飞龙实和子 想一的母亲,已故。
池尾沙和子 实和子的妹妹,想一的养母(54岁)
辻井雪人 想一的从表兄弟,小说家(28岁)
仓谷诚 研究生(26岁)
木津川伸造 按摩师(49岁)
水尻道吉 管理人(68岁)
水尻柞 管理人的妻子(61岁)
架场久茂 想一童年的朋友,大学助教(34岁)
道泽希早子 学生(21岁)
岛田洁 想一的朋友(38岁)
序幕 岛田洁的来信
飞龙想一先生:
(前略。)
听说你安然无恙出院了,是吧?前些天收到了令堂的信。太平无事,这比什么都好。
本想跑去祝贺病愈的,但俗事繁多,目前还不能如愿。姑且用书信问候,敬请原谅。
想永葆青春,但到今年5月已经38岁了。认识你是我22岁的时候,所以将近16年了,用一种陈腐的说法,真是光阴似箭呀!
至今尚无计划结婚,也没有找到固定工作,也许迟早会继承寺庙的,但我父亲还健旺着呢,真是不好办。说这话会遭报应吧?
我呀,依然是到处奔走,好管闲事,常招世人嫌弃。要说是任凭旺盛的好奇心,不大好听,但总而言之,自幼就有的爱跟着起哄的本性真是难移呀。哎,自以为上了年纪多少能克制一些了,可是……
今年4月由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又卷入了意想不到的事件。那是发生在丹后半岛的叫Txx的村落边上的“迷宫馆”里的一起凶杀案【注】,媒体也好像炒作得比较厉害,所以说不定你已经从什么报道上知道了吧。
说来不吉利,最近两三年我所到之处都碰上这种事件。总觉得自己像是被死神缠住了似的……不,不对。我甚至半认真地想:被死神缠住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建筑家建起来的那些房子。
去年秋天我去医院探望你时,跟你说了吧?名叫中村青司的建筑家的事;他建起来的那些奇怪的建筑物的事;还有在那些馆里发生的几起案件……
当时刚参与“水车馆”事件后不久,所以我也好像相当兴奋,也许不合时宜地说过了头。一来住院期间连读书都被禁止的你好像非常无聊;二来你说你知道那个藤沼一成和藤沼纪一的名字【注】,所以不由得关于中村青司这个人物及其“作品”,你好像也很有兴趣吧,大概是同为艺术家,或是因为有什么东西被他吸引了吧。
不过,你还会画画吧?
请你忘了不愉快的事,画出好作品来。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喜欢你画的画。关于美术,我几乎是门外汉,但我认为你的画确实有某种独特的魅力,例如好像与“水车馆”中看到的藤沼一成画家的幻想画有共同之处的一种妖艳的魅力。
连篇累犊地写了这些无聊的事。我想迟早会有机会去你那里的。
如有事请跟我联系,用不着客气,我会高兴地参与商量的。
再见。请代我向令堂问好!
岛田洁
1987年6月30日
…
【注】请参照《迷宫馆的诱惑》
【注】《水车馆幻影》中登场的幻想画家及其儿子的名字。
第一章 七月
1【注】
我来京都,那是7月3日星期五下午的事。
6月已经结束,但尚未出梅【注】,那天也从低垂密布的灰色的天空中不停地下着温温的雨。线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新旧楼房、模模糊糊地黑黑地浮在那背后的山影、挤满狭窄道路的车流、白色的高得让人觉得不合时宜的耸立着的塔……从列车模糊的窗口看到的这些风景,仿佛是摄影机摇晃时拍摄的一个个静止镜头似的。
(多暗的城市啊!)
城市与自然恰恰相反,由于长时间淋雨而渐渐失去了它的生气。季节和气候形成的这景象,原封不动地成了我对古都的第一印象。
京都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来过一次。那是在遥远得记忆中已经没有了的过去——也忘了是什么季节,大致当时这座城市也下着雨,我想那时一定是抱着和今天一样的印象。
“讨厌的雨……”穿着淡黄色白点花布衣服的母亲用手帕擦了擦浮在白皙额头上的汗珠,说道,“叫辆出租车吧——想一,身体有没有事?”
我晕车晕得厉害——特别是列车。在从静冈上车的新干线的列车中,自过了名古屋一带起,我就觉得恶心起来。
“没有事。”我小声答道,重新拿了一下行李,但在向台阶走去的匆匆忙忙的人群里,我的双脚有点摇晃起来。
一出车站,重新仰望了一下天空。
雨不住地下着。雨声和周围的喧闹声不停地响着。母亲说“讨厌的雨”,但我倒觉得这雨声十分难得。
古都、京都——我父亲出生并去世的城市。纵然如此,也没有涌上什么感慨。
不用说是大学时居住的东京,就是对曾经去过的几个城市,甚至是我出生的故乡静冈也从未感到过留恋。城市就是城市——哪个都是陌生的人们聚集的空间,而且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是心情舒畅的场所。
“想一。”母亲担心地朝斜望着天空伫立不动的我喊道,“怎么啦?还是不舒服吧?”
从去年夏天到上月中旬,我身体不适,不得不长期过着住院生活。抑或这个缘故,出院以来母亲格外地担心我的身体情况。
“啊,不。”我慢慢地摇了摇头,对着个儿矮小的妈妈那细长清秀的眼睛回了一个微笑,“没有什么。出租车站——啊,在那里。走吧,妈妈。”
父亲出生的城市。父亲去世的城市。
父亲飞龙高洋去世,那是去年年底的事。听说是62岁。可是,我最后见到他究竟是何时呢?25年——不,或许是更久以前吧!
对于容貌,甚至是声音我都记不清楚的“父亲”——遥远的记忆鲜明地留给我的,只是他那总是朝自己儿子燃烧着冷淡光芒的眼睛。
2
从名叫白川大街的大道进入靠近山的地方,拐过几个拐角。从京都车站乘出租车大约需30分钟。说是左京区北白川,但完全不熟悉京都地理的我,不清楚那是在市区的什么位置。
山就在近处,所以大概是在城市的相当边缘之处吧,我漠然地这样想道。
一派幽静的住宅街风景。
稍稍倾斜的道路两旁是绵延的土墙和树篱。谁家都有相当大的地基,几乎听不到大马路上车子的声音,大概是下雨的缘故吧,也没有在道路上玩耍的孩子的身影。
“挺好的地方吧。”母亲一面给下了出租车的我打上伞,一面说道,“很安静,交通又方便……”
雨停了一会儿。小小的雨滴随着缓缓的风白花花地摇动着,犹如雾一样。
“来。”母亲迈出了腿,“是这儿。”
用不着母亲说我就知道,因为在建于一片浓郁的山茶花树篱缝隙间的石头造的门柱上,贴着写有“飞龙”二字的褪了色的门牌——这是一幢平房,很是古老的日本建筑。
大概长时期没有修剪吧,庭院里树下丛生的杂草长得高高的,灰色的踏脚石一直延伸到正门口,从枝繁叶茂的樱花树的间隙中隐隐可见发黄的用灰泥涂抹的墙壁。灰色的屋顶大瓦被雨淋湿后闪着黑光,整个房屋像是在滚动似的贴在地面上。
母亲把伞一交给我,就先沿着踏脚石往里面走去。我跟着她到达屋檐下时,正门口的拉门的锁已经被她打开了。
“把行李放在屋里,”母亲边说边打开大门,“先去一下公寓……先得向水尻打个招呼呀!”
跨进门的一瞬间,视野突然变暗。屋里竟然暗到了这种程度。
进门处的土地房间很大——花了一些时候眼睛才习惯到能实际感觉到它“很大”。一股酸了似的发霉一样的老屋子特有的味道,傲然飘荡在空气不流畅的黑暗中。
土地房间延伸到右侧的里头。正面的里头和左侧可见白色的隔扇,所有隔扇都严严实实地关闭着。
我横穿过昏暗的房间,打开了正面的隔扇,里面就是设有放任何家具的空荡荡的小房间。
父亲一直住在这里——这个昏暗的家里吗?
将提在手里的旅行包往那屋里一抛,我就急忙转过身去,仿佛想逃脱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那绝不会再有的视线似的。
就在这一瞬间,我不由得两腿发软,甚至差一点儿发出喊声:那东西立在一进正门的右侧的墙壁边。由于在暗处和那地方刚好是死角,所以刚才没有察觉到。
那是一名女子——恐怕是年轻的女子。
说她年轻,那是从她的体态推测的。身材苗条、匀称。丰满的乳房、细细的腰……只是她没有“脸”。头部倒有,但那上面没有眼睛、鼻子,也没有嘴巴。斜向着这边的面孔是张白白的、没有起伏的扁平脸。而且一丝不挂的身体上缺着一条胳膊。身体曲线在肩膀处不自然地断了。
“人体模型?”——她不是活人。是人体模型——百货商店的柜台和时装商店的橱窗里立着的那种东西。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放着这么一个……”
“是你爸爸制作的。”站在门口的母亲回答了我的疑问。
“父亲制作的?”
“唉。这家里还有好多个呢。”——因逆光没能窥见她的表情。
“为什么他制作这种人体模型?”
“这……详细情况我不知道……”
我的父亲飞龙高洋曾经有一个时期是颇为有名的雕刻家和画家。如果是关于不是作为“父亲”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他的知识,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也是有的。
他1924年生于京都,违背实业家的父亲飞龙武永的意向而立志美术,1949年25岁那年结婚,并离开父母移居静冈市。在武永死后又回到京都,把京都作为其创作活动的场所。
在雕刻方面虽然用正统的素材,但制作非常抽象而难以理解的作品,另一方面又以细腻的笔致画一些写实的静物画。极度讨厌与人交往,被视为怪人,但听说例外地与家住神户市的著名的幻想画家藤沼一成有亲密的交流。
完全第一次听说他制作了这样的偶人,而且偏偏是人体模型……我总觉得那是一种跟他在雕刻中的兴趣和作风完全沾不上边儿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他制作起这种东西来的呢?而且那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或许,这是由于对雕刻家飞龙高洋的基本认识不足而产生的疑问。总而言之,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真的是很有限,因为特别是这十几年——自开始理解自己对他来说是何种存在以后,我一直竭力不去想他,作为儿子,也作为一个自己也拿笔的小小艺术家。
“走吧,想一。你是初次来,还是从外面绕过去的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