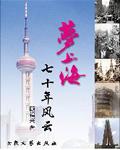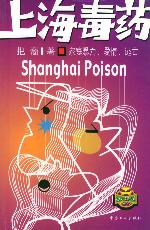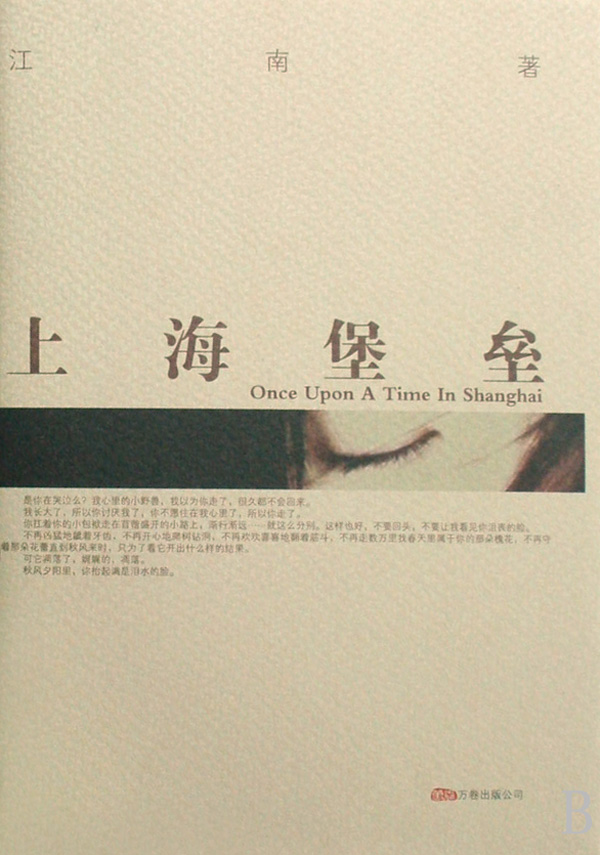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机放在一起,像考古学家在雅典地下挖出来的碎片一样。而由什么小工厂加工了十几件同样的假货,放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卖着。也没有人再轻轻地拉你一下,告诉你什么他有要杀头的东西,一动,他拿出一张生产证明来证明自己不是批发来的东西。
再去旧货街,发现那里的老房子上,个个被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拆”字,那个街区要改建了,老房子将没有了,市场当然也要没有了。那次去,带着一架照相机,爬到一个高处,想为流水一样失去着的地方照一张相,从镜头里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红色的“拆”字。
弄堂里的春光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人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临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蹋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一八七二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像里面还有许多小国家一样,就像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人,仔细地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地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脸相。所以,在上海从小到大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是了解上海的某一块地方。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中层阶级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可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可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的娱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他们定定心心地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可一眼一眼地膘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阉的成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城市镜子里的家乡人
一个人无法自己看见自己,只有站在镜子前面,才靠着本来和自己没有相干的玻璃和水银,发现自己的眼睛原来不是书上写的黑色的眼睛,而是深棕色的,只有瞳仁是黑色的。
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到本来没有相干的外国去了,然后就会像站在镜子前一样,从陌生的城市里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穿着一双北方的红皮靴子到上海,在上海成长,可并不了解上海,也不喜欢了解它,我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过路人,早早晚晚是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可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歌里唱着的那故乡的小河,我没有。那小红皮靴子早穿白了鞋头,送给了收旧货的安徽老头子,我把它当成故乡来怀念。就这样忽视着自己天天生活着的地方,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结束了,我有了自己的褐色护照,飞机斜着飞上了天,越过了山,越过了海,越过了许多城市和树以及红绿灯。飞机比地球转得快,它一直往西飞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多过一个夜晚。我以为自己从此是到广阔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去找自己的故乡,其实却找到了镜子,看到的是那镜中的家乡。
对我来说,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生活二十年而对它视而不见,又可以让这个人把三十岁以后的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它的探索上,在咖啡馆里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和疑问。每次拖着箱子回来,总是再去找笔记里问题的答案。它就是那个能够让一个人把这样的旅行延续一年又一年,将一年年辛苦挣来的钱大半用光在旅途中的城市,它对我来说真了不起,每次虹桥国际机场那白色的大飞机大吼着冲进沾着污染的白云,我大多是去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带着不同的计划,可是看到的,还是它。只是它有所不同,就像在一个人的心里发生了新的爱情,那样的不同和那样的惊喜。
圣彼得堡与上海红色都市的浪漫
彼得堡有一种只有红色国家都市才会有的浪漫,凋败的、梦幻的、稍微过了时的古典,洋溢着孩子式的激情,单纯而固执,就像上海。
在圣彼得堡期间,我住在一栋绿色的大房子里,楼厅的四角有巨大的雕像,男人和女人,裸体的,很大块的肌肉和卷发,雕像低头抵着天篷,像是用力撑着天篷,他们的颊,鼻子,肩膀,乳房,脚趾,一切隆起的地方都落满了灰。那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宅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倒了,贵族跑了,他家的房子被不相干的人住了快一百年,从来没有维修过。楼厅里有一个老式的电梯,用的是拉门,黑色的铸铁纹饰里结满了灰尘。那种灰尘腐蚀着生铁的甜腥气味,那种日久失修的电梯井里随着拉索吊上来的咸湿气味,我从德国去的圣彼得堡,这德国电梯里断断没有的气味,在我是那么熟悉,那是上海老公寓里电梯的气味。在头顶上吱吱呀呀的钢索声,让人担心下一分钟它就会断了,那是在老公寓的电梯里天天担心的事。
我住的房间原来是一大间起居室,后来的房客用木板分隔大起居室,一间做卧室,一间做画室,还有一半做客厅。躺在沙发上,能看到天篷四周那精巧的纹饰,用薄木板做的墙只做到它的下面为止,为了省事以外,一定也是不舍得遮了它。还有走廊灯照亮的门玻璃,刻花的玻璃在门上闪闪发光,像从前的钻石一样。现在门上的木头被磨毛了边,又胡乱钉了门锁、插销和挂锁,那玻璃像灰堆里的豆腐一样。
外面是长长的走廊,要是出去以前不把自家的灯打开,就比照相店的暗房还要黑,走廊里堆着木箱子、纸箱子,每一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