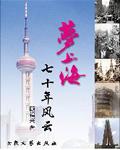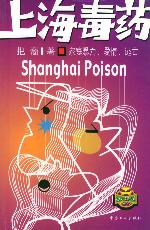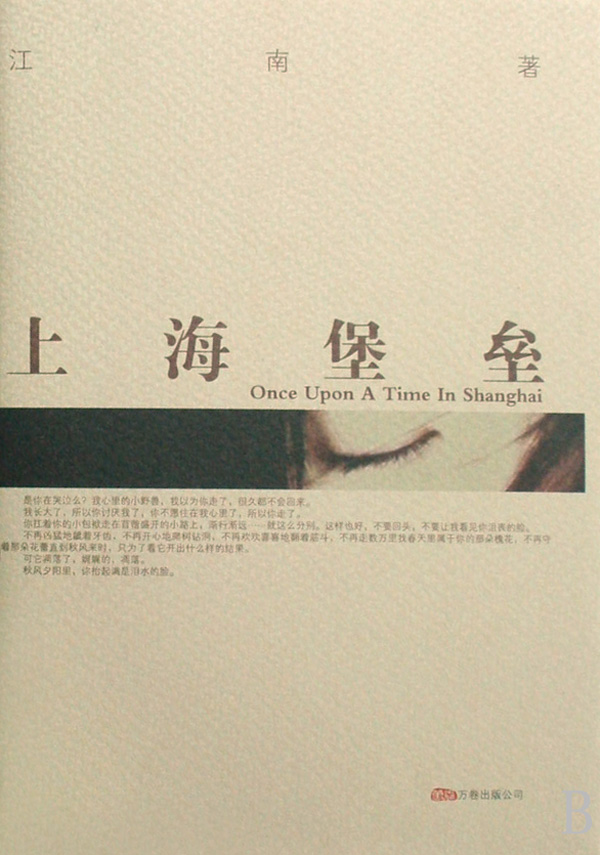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甚至还看到上海名妓在房中抚筝,圆圆的脸上有一种灵动的神情,眼光温柔如水,眼角像中国亭子的飞檐一样,高高地向鬓发挑过去,接下来的一张,是她倚在一张法国卧榻上,像拿破仑妹妹一样的姿势。可她更宁静,看不见恣肆的欲望,也没有风尘气,她应该是卖艺不卖身的书寓。要是她就是因为偏好接触洋人,而渐渐学会说英语的陆兰芬,外国人那时称她为“支那美人”,是没有叫错。
当时,大概传教士是在中国真正接触中国民众的外国人了,听说他们传教不光是在教堂里,而常常走到教徒家里,走到中国人生活的地区里去。有书上说,在女孩子出嫁的第一夜,传教士常常会和女孩子单独呆上一夜,向她传教,并让她把上帝带到婆家去。当时的江南竹枝词,对外国传教士的这种作为,多有讥讽。而在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早早地设法建立了一个海外的欧洲,把自己小心躲在里面。一个爷爷在上海度过青年时代的德国女子告诉我说,她的爷爷晚年回忆上海时曾非常怀念上海,可是他不喜欢豫园周围的中国城,他说那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去那地方,因为觉得在中国的街区中国人的文化里,不那么自在,也不那么安全。也许就因为他的传教士身份,才在这本相册里有不同阶级的中国人很私人化的生活照片。他甚至还领着一大堆朋友去了豫园,他们在假山上照了相,像中国的中学生去豫园玩常常会做的那样,大家在湖石假山上各自站好,留下的照片,像一群猴子在猴山上,即使他们庄严地穿了齐膝的礼服,还拿着手杖。
在差不多相隔了两个世纪的上海,那个下着冻雨的下午,我小心翻着偶尔保留下来的相册,想象着从前用照相机留下这些照片的那个人,那个传教士。我老是看到那个穿旧式长裙的女子,渐渐地开始想象那个为她照相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
从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长满了野草的京城大殿和坚实的长城;看到了木头铺的上海城隍庙的九曲桥;看到满街挂着娟秀毛笔字幌子的南京路上,一个大汉肩扛着年轻的妓女出局,现在这张照片可以在各种版本的上海史书里看到,原来是出于这里;看到了一台崭新的燃气火车头在中国大地上像刚擦好油的新皮鞋一样闪闪发光,下面有个穿马褂垂小辫子的男人默默地看着它放出大团白色的气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设想的那样膛目结舌;还有长江上的小扁舟海上面立着一些缩着肩膀的鱼鹰,撑着船的,是面容古朴的男人,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穿着斯文的大襟褂子;甚至还有一架美丽的花轿和花轿下的新娘在乡野的阳光下活泼地站着,后面乱乱地跟着一队人,拿着东西,抬着东西,远远地从一片田地的垄上走来。在他眼睛里的中国不那么满目创伤,而有一种风尘仆仆里的安详无争以及伟岸,实在是像一个久睡的狮子。那时的天空好像比现在要清朗许多,万物都那么清晰,河水清亮地倒映着太阳光,植物的表面发着油亮的光。他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喜欢宏大的构图,很少有特写,北方的一殷长城在画面上游龙走蛇,雄壮而飞扬。在一百多年以前,是什么样的传教士,受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有这样好的照相机,这样好的摄影技术?我想,他并不是一个仇视中国的人,他的镜头很严谨,没有贬意。
相册里的照片,渐渐多了一条平静的大江,江上有帆船。然后里面有了红顶的官吏带着听差在路口迎候的照片。那年轻的官吏严肃而谦恭地看着前方,四个听差举着托盘,里面装满了中国古代的金银宝贝,我看不懂那些到底是什么。这次旅行一定是受到了中国官府的礼遇,以后,他为祈年殿照了相,甚至还去了颐和园,那是老佛爷的花园,他远远地为湖边的铜牛照了相,还有许多高官迎送的场面,那些清朝的高官,穿着貂皮斗篷,沉着色厉内荏的脸。这是照片里面出现过的最难看的脸色。甚至还有进了皇宫的照片,他用闪光灯照了高悬着“正大光明”的大殿,还有汉白玉石阶中间的盘龙浮雕。他参加了许多列强与清朝政府接触的场合,这也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在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外国公使晋见皇上的情形,从那些背影看,公使们的仪态远比电影里的文雅有礼,皇上看上去也不那么懦弱。
历史书上说,上海的徐家汇天主教区,是西教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重要基地,我想这该是没有说错。他们从上海去了北方,照片上沿江的新教堂上,有一个在法国的北部常常可以看到的彩色玻璃大花窗,和麦茨的教堂玻璃花窗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去了日本,印度,还有朝鲜和台湾。他们还去了中国的庙。因为有许多张照片是寺庙,其中有一张,是隆重地披着袈裟的和尚和许多年轻的小和尚,看上去他们迎在大殿外面的空地上,他们双手合十,望着镜头,或坦然,或逼视,或戒备,或诸问,他们的眼睛不那么友好,可是有礼有节,姿势谦和。那是中国传统的含蓄。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以前面对外来文化的眼神,他们全然没有同时代中国民众面对同一架相机的那种天真。
这个传教士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时的一部分中国,一页页地翻着照片,好像渐渐地就感到了他的角度和他的眼光,他从来不用人为的仰视或者俯视的角度,他构图精良,他对眼前的事物有一种发现的惊奇,就像隔了许多时代,又翻开了他的照相本的我,面对他的照片的心情。他虽然死去多年,可他那时看中国的目光,还在相册里活生生地闪烁着。
又是一个阴雨的下午,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画册,关于上海历史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在一个中国庭院里围桌而坐的两对男女,一对是中国人,另一对是外国人,那个女人穿着深色的长裙,她的脸让我熟悉,她的眉心里有一些细小而坚毅的皱纹向额头爬去。然后我想起来她就是从法国教区流落出来的照相本里的那个女子。然后我看到她身边的那个人,穿着教士的黑色长袍,腰上拖着有流苏的带子,细高个子,留着络腮大胡子,长长的脸上,有一对大张着的眼睛。照片下有一小条说明:“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夫妇和上海地方官员”。因为相册上的女子,我终于见到了他。他放在桌上的手指是细长的,就是它们为了那本相册。按动了许多次的快门吧。可这张照片又是谁照的呢?
上海人杜尔纳
杜尔纳先生坐在露天的咖啡桌子前,抱着他那高大的狗。他很老了,他老得眼角向下重重地落下去,显得那犹太大鼻子更像悬挂在脸上似的,从前看欧洲战争的小说,纳粹杀人的时候,常常说:“一看你的鼻子就知道你是犹太人。”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在上面用中文写下自己的名字:“杜尔纳”。难为他,那个“尔”,还是用繁体字写的。
他看到和我一起去的皮克夫人,便用奥地利德语问她是不是去了萨尔茨堡的会议,那是上海犹太人的一次重聚活动,一九三七年以后,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坐意大利船逃往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上海接纳了二万五千个犹太难民,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大难民人数的总和。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国际犹大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回到欧洲。他也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
他是奥地利人,欧洲排犹开始的时候,他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一九四○年经历了从奥地利翻过雪山逃向瑞士,在当时的中立国他找不到地方住,找不到地方工作,瑞士没有把他送给纳粹,但不给他生活下去的可能,它像雪山一样美丽晶莹而寒冷地旁观他的挣扎。于是他从瑞士再逃往上海,在当时的法国租界里一条高尚的街区落了脚,弄堂里的中国孩子在他上街的时候常常迫着他叫“大鼻头伯伯”,那是种孩子温和的戏慝,惹他注意他们。一九四三年他被日本军从复兴中路的住宅赶进虹口犹太人隔都居住,直到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他离开虹口犹太人隔都,和中国妻子一起住在徐家汇,他在上海结了婚,有了家,学会写中国字,喜欢吃上海的家乡小吃。一九五二年,他随最后一批犹太人离开上海,他和妻子去日本,在日本生活七年以后离开日本去美国,在美国生活了三年,离开美国回到故乡奥地利。所以,他会说奥地利德语,日语,美国英语,卷着他的舌头。他说着说着,突然对我说:“不过,伲是上海人。”
他说了一句老式的上海话,然后,他说起了上海。
有时夜里做梦,又好像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法国梧桐树,在夏天的时候把太阳全都遮住了。复兴中路上有一个法国公园,里面的玫瑰园在黄昏时候香到园子外面来。拉都路上有一个犹太新会堂,里面有高背木头椅子,听拉比传教的时候可以很安静,听说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发生了火灾,把会堂烧毁了。
我说新从法那是我中学时代的大礼堂,我们排着队到大礼堂去听报告,总是把身体缩到高背椅子里面,这样,老师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有时我们到礼堂的楼上去唱歌,楼上全是褐色的护壁板,一走动,老地板就吱吱地响,尘土飞扬。当时我们都知道原来这是个教堂,可不知道是犹太人的。同学们都不敢一个人上楼,觉得的些幽暗的角落下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说沿着那条路走不远,就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餐馆,老板也是从奥地利逃过来的,里面的东西好吃,所以在上海很有名,听说那时在上海很红的宋家姐妹,也去那里吃过饭。在窗台上,逢犹太节日,就点上犹太人的九枝蜡的铜烛台。周围还有一个犹太人医院,有从欧洲来的最好的医生。还有一个犹太人俱乐部,即使是在战时的上海,遇到节日,犹太人也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用水梳齐自己的头发,到这里来开舞会,那里的地板是细条子的,房屋高大,窗外有花坛。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忘记这里是上海的什么地方。
我说是的,现在那个餐馆找不到了。那时的医院,现在是上海五官科医院,当时的房子,现在还在用着,刷成了白色。那犹太人俱乐部,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栋楼。风尘仆仆,细条子的地板现在仍旧平滑如初。外面的花坛现在也还是花坛,只不过里面的玫瑰花,现在又瘦又小,种已经退化了。有犹太人留下来教中国人小提琴,成为音乐学院的提琴教授,而上海音乐学院的提琴,一直是强项。一九九四年上海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上海重聚的时候,他们还特地回犹太人俱乐部参观,当年的人拿着照片回来,照片上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在上海长大的孩子,在上海有了爱情的青年,现在平安地生活着。
“跳舞的时候也会有惊险的,那时晚上上海灯火管制的,开灯要先拉黑布窗帘,要是忘记了,外面就有宪兵叫,将电灯暗掉。”杜尔纳先生说。
我很吃力地听着他的话,他常常不自禁地把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