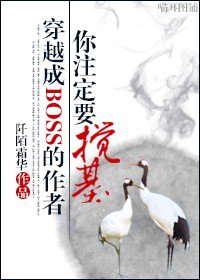天浴 (作者:严歌苓)-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杨麦说:“谁让你去掉泪了?”
她说她这么多年没给自己买过内衣内裤,都是捡杨麦的破烂改成内衣内裤。
杨麦说:“我说了多少次,叫你别捡破烂?”
“你吃的西洋参是我骑车跑二十里路,到中医学院给你买的!我顶着大太阳,骑了两个半钟头,马路上的柏油都给太阳晒化了,糖稀一样,我不照样骑吗?回到家眼都黑了,背上褂子潮了又干,干了又潮,你杨麦喝红枣洋参汤,我小顾碰过一根参须没有?一头驴子冒毒日头跑几个钟头,也有人喂把料给它吧?我是个人唉!……”
杨麦说:“你愿意大太阳下骑车去跑!明明有公共汽车不坐!你就是要唱苦肉计给人看!”
这句揭露性的话太恶毒了,小顾体无完肤地愣在那里。过一会,她满心悲哀,想杨麦怎么总把她看那么透,给他一点拨,她也觉得自己含辛茹苦,样样事情做得过头一点,就是希望能让杨麦欠她些情分。小顾只有在杨麦做人下人的时候,才是自信的,自如的。老了胖了的小顾,看着如日中天的杨麦,心想可别再出来一个女老师。现在的杨麦不仅有名有钱,长到四十多岁,刚长得须是须眉是眉,长出一点样来。
杨麦的求爱者各行各业都有。其中一个才二十来岁。杨麦跟她恋爱不为别的,就为他们巨大的年龄悬殊。在中年男人那里,悬殊象征成功、荣誉、金钱,也象征体魄、魅力、雄性荷尔蒙。年轻女人都是苍蝇,多远都能嗅着荣耀、成功、金钱而来。来了这后,又被体魄、魅力、雄性荷尔蒙黏住。
二十来岁的女孩是个女大学生,她可不像女老师那样软弱。她先逼杨麦,逼不出结果就去百货大楼找到了小顾。她走进小顾的科长办公室,看着头发烫焦、衣服绷出横折子、高跟鞋打晃的小顾说:“噢,你就是小顾吧?”口气又大方又皮厚,把原本皮也不薄的小顾都震住了。
小顾当然知道女大学生的存在,但她没有太多声讨过杨麦。因为杨麦一旦对她做了亏心事,在家里就老实一些。吵起架来,小顾也多一个杀手锏。小顾自己也有过丑事,这方面和杨麦一样经不起追究。小顾领头向办公室外面走,她不想让同事知道她小顾不是百分之百的杨麦夫人。
女大学生跟着小顾走到楼下院子里,用简单的几句话请小顾让位。
“你说什么?”小顾抬起眼。眼睛清亮天真,不谙世事,睫毛又黑又长,是难得的美目。可惜杨麦很久不去看这双眼睛了。不然他会心颤,像他最初爱她一样。会想,那里面有多少善良,而善良往往混着蒙昧甚至愚蠢。“你再说一遍。”
女大学生又说一遍,更简洁明了,更厚颜无耻。
小顾甩起巴掌打过去。女大学生马上捂住腮帮。小顾的手已回来。又是一巴掌。就这样,女大学生和小顾一退一进,小顾左右开弓,女大学生嘴里直叫:“唉,怎么动手?……”
小顾打得好快活好暖和。心里冷笑,这类女秀才都是窝囊货,就会讲点馊语写点酸诗,拿不出行动来。这位嘴尖皮厚一身柴禾的女学生能有什么用场,上不了床,下不了厨,杨麦怎么找这么个大当给自己上。
一架打完,杨麦跟小顾正式提出离婚。
小顾随他去捶胸顿足,说他和她生活十几年如何痛苦,她只是照样给他做饭、洗衣、煎补药。局面就这样拖下去。拖得女大学生跑了,换成了个歌舞团的女笛手。
这两天儿子回来对小顾说:“你别拖爸了。你要把他拖死啊?”
小顾傻了。
儿子现在十七八了,都是郁悒艺术家的苍白模样。小顾常常奇怪他们没有她的活力,她的健康。
大儿子说:“爸要把你们的离婚案提交法院了。”
小顾样子乖乖的,看一眼大儿子。
小儿子说:“爸知道你的事。”
小顾顿时垂下头,又感到那阵丑恶皮疹一般在脸上发散开来。她想她的儿子们一定看得见它,她只得戴着这层丑恶把头垂得低低的。
大儿子说:“爸问过蔻蔻、穗子她们了。她们扒在楼顶栏杆上看见好多事。爸刚放出来的时候,就去问过她们……”
小儿子说:“你拖爸的话,法庭把你的事公布出来,我和哥就完蛋了。”
大儿子说:“照顾一下我们的名誉,我们要脸。”
小顾一点一点冷下去,任大股泪水在她鳔着一层丑恶的脸上纵横流淌。
她没有向杨麦去声辩。和黄代表一场艳史,她是不得已的,她的出发点并不丑恶。或许那就更加丑恶。
小顾什么也没说,便在离婚协议书交上法庭之前签了字。
十几年后穗子回国,在曾经的“拖鞋大队”伙伴家见到了杨麦和他的年轻夫人。这位新夫人不比初嫁时的小顾大多少,杨麦对她说话口气总有些冲,笑容也很不耐烦,让人明白他宠她是没错的,但绝不拿她当回事。杨麦对其他艺术家协会的老同事很当心,这表现在他过分的随和与过分响亮的大笑。因为这帮人里只有他一个还有名利可言。他为自己的好时运感到不安。小小的杨麦太太年纪不大,却很懂得杨麦此刻的用心,帮衬杨麦把玩笑开得更好,以缓冲随杨麦的财运、官运、艳福而来的孤立。打了一下午牌,主妇安排了晚饭,大家都喝了一些酒。小杨太太以掐耳朵,捏手指来阻止杨麦喝酒。杨麦喝红了脸,不时哈哈大笑,但两人都让大家明白,她敢这样闹只是因为他由着她闹。穗子看着幸福的杨麦夫妇想,当初小顾真是兜了一个大弯子兜到这群人里来了,不然杨麦可以提前幸福多少年。
饭后杨麦喝醉了,被扶到长沙发上躺下。大家恢复了聊天,听杨麦叫起来:“小顾,小顾,倒杯茶来。”所有人静下来,小杨太太脸上有点挂不住。过一会,杨麦起身去厕所呕吐,小杨太太跟进去捶背,老三老四地轻声唠叨他不该喝那么多。杨麦又躺回到沙发上,小杨太太拿一条毛巾挨着他坐下来。人们该聊什么还聊什么,但气氛有一点不自然了,都开始逗小杨太太,又逗得不十分高明。一直低声呻吟的杨麦又叫起来,“小顾,小顾啊,”叫得体己贴心,似乎醉成这样,叫叫也是舒服的。
小杨太太用湿毛巾擦了擦他的脸。原来小顾阴魂不散,这让她措手不及。所有人都有些尴尬,都不知接下去怎样再打圆场。“小顾啊,倒杯茶给我。”杨麦说,耍点少爷腔调,并明白不会为这腔调付代价的。这是另一个杨麦,松弛舒坦到极点的一个丈夫。让在场的人意识到,曾经他和小顾间的亲密,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不久杨麦醒了酒,让小杨太太扶走了。没人把他醉酒时的表现告诉他。穗子猜是大家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去讲给清醒后的杨麦听。
但不知是谁把它告诉了嫁到了深圳的小顾。小顾的现任丈夫是个大工厂厂长,很为自己老婆是著名画家杨麦的前妻而骄傲。小顾总是告诉她新认识的人,她就是爱杨麦,他多不是东西她也爱,她也没办法。她讲这话时火辣辣的,毫不在乎自己的牺牲品身份。似乎只要她一头热着,杨麦就有她的份。这种时候,她的微笑里藏着一点玄机,一点梦,说:等着吧,还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别人等或不等,她小顾反正是心笃意定地等着。
《我不是精灵》
那事过去十年了。许多人说我几乎是一夜间长大的,从那事以后。
当时我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我爸,他走了进来。
他不高,眼睛很逼人。他在想:她是谁?年轻到了傻呼呼程度的一个女孩——十七?十八?……差不多,我刚满十九。他还想:老萧蛮子那副脸模子长给一个女孩倒相宜了。老萧蛮子是我爸的别名,他写打油诗时用的。假若我爸和我妈没分居,假若旅馆不客满,老萧蛮子不会与他搭伙住在此地,我也不会在此地遇上他。此地叫西晓楼,号称艺术家避难所,多数画家作家文革中流离失所,回城没房住,便暂时落脚在西晓楼。我们刚想互相礼貌一下,电话铃响了。他从我第一句话就确信了我与老萧蛮子的关系。
我指控我爸存心躲避一场事关重大的谈话。学校一放暑假,在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准备了一肚子词来干涉他与我妈的关系。他说他不爱我妈;我说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讲什么爱不爱,快回家吃我妈腌的咸鸭蛋去吧。文人们刚从“红卫兵”、“军代表”、“工宣队”手里活出来,他们头件事就想起爱不爱来了;刚刚皮肉不痛苦,感情就“痛苦”起来。我妈纵有一千个不是,但千里迢迢把咸鸭蛋送到他那“流放地”,还是很动人的吧。
我爸在电话里说:“别扯那么多淡话,你快出来!你小韩叔叔有要紧会面在那房间里……”
“谁是我小韩叔叔?”刚才那个英俊的矮子?
我爸用不得了的口气说道:“他是韩凌!画家韩凌呐!……”
听我这边不作声,他更急地叫:“你快出来,别在那里捣乱!小韩叔叔下午两点要会见一个女朋友!”我挂掉电话,他从洗手间出来,朝我微笑。我怎么也喊不出口什么“小韩叔叔”。与他握手时,我发现他少了根手指,其他没什么不寻常。他虽不高大,却十分匀称,微笑如一般中年男人那样多少带些心事。
刚开门,迎头撞上路淮清,她是我要好同学的长姊,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她后面跟了个苗条女子,脸不太年轻了,却梳着齐眉刘海。我想弄清她俩究竟谁来相亲,便磨蹭着越走越慢。
淮清说:“干嘛走呢?穗子,我们都是来向韩老师求画的!”
“哪里好意思啊,韩老师的画滴墨千金!”齐眉刘海说。两位女士都在脸上涂了粉,也都仔细打扮过。几年前毛主席过世后,街头一下子添了许多涂粉的女人。
“穗子,”淮清对我说:“她叫张叶。”她停下,等我反应。见我呆得过久,又说:“她演过电影啊!”接着报出个把莫名其妙的电影名字。我忙深吸一口气。我不崇拜,但捧捧场逗人家高兴还是善良的吧。画家领我们走进里屋。这屋挂了些裱过的画,一幅是两只猴,一幅是匹卧骆驼,第三幅是条狗。狗上题款道:“纵是无语也可人。”我对着画长时间出神,觉得画里有种难懂的情绪。画家的技法很独特:将动物作静物画。画看去平面、滞板,色彩极暗,你却完全大出所料地在凝重色彩里发现一点腥红或翠绿,或一抹无来由的碧蓝,于是一种勃然感便有了,一种带有鬼气、灵光的勃然生命便出现了。看这些画你木木地看进去,直看到心被什么砸一下。
这时听他们那边聊得热闹起来,似乎在谈画家的个人画展。我想去参加他们谈天,却很难从这些画上分心。很快又听见两位女士激动地讨论,要画家为她们画什么,画家却说:我画,你们只管看,喜欢就拿走好了。她们忙说:啊呀,韩老师的画哪里有不好的!我走过去时见画家在一只砚台上反复运笔。突然他将笔一提,那么用力,如同拔出什么。张叶还在说笑,淮清捏捏她胳膊。当他一笔挥下去,我情不自禁“哦”了一声。画家看我一眼,那目光竟有些感激。似乎他那一腔情绪并非白白挥洒出去,它被什么盛接住了,好比那种感应墨色最理想的纸盛接他的笔。
他居然停下来,就这样看着我。他倾向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