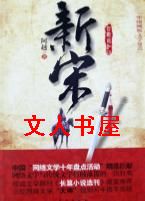新宋-第5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来……”范翔连忙跟着勒马,他这时总算知道,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何人。
“承平之时,要讲礼义诗书,否则出使难免辱国;但有事之时,却不能用书呆子出使。不过,我方才有意试探,仲麟终还是沉不住,亦算不上上佳之选……”潘照临毫不顾忌范翔的自尊心,他言下之意,分明是说范翔亦不过是勉强凑合。范翔听得又是羞愧,又是哭笑不得,却见潘照临挥鞭指了指远处的一座亭子,道:“我给仲麟引荐一个人。你此行之使命,便是要设法将此人不动声色的引荐给辽主或他身边的重臣。”说罢,策马朝亭子那边跑去。
范翔连忙吩咐了一下使团,驱马跟上。
在亭子里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和两个僮仆,男子的衣饰很平常,但范翔早就留意到亭子外面的三匹高头大马——无论是在松漠庄,还是在雍王的马厩,如此高大的白马,都是很少见的。
“在下柴远,见过范大人。”那男子见着范翔,连忙抱拳行礼。
“柴远?”范翔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但此时亦不及细想,便见潘照临挥手斥退那两个僮仆,道:“仲麟需记住一事,柴远并非朝廷使节,与大宋并无半点关系。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商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才设法接近辽国君臣。是以,此事若令朝廷知道,连仲麟亦难免要受责难。”
这种要求,未免强人所难。但范翔听得出来,潘照临并非是想针得他的同意,“但在下是首次使辽,要不辱使命,没有大苏协助……”
“仲麟若不怕回国后被问罪,尽管去找大苏,他身边有多少职方馆的官员,想必毋须我多说。何不干脆向朝廷拜表直接一点?”潘照临不待范翔说完,便毫不留情的讥讽道。
但范翔此时却已顾不得潘照临的讥讽,急道:“然……”
他才说得一个字,又被潘照临打断,“去找朴彦成。”
“朴彦成?”范翔奇道。
“便是朴彦成。”潘照临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望了范翔一眼,仿佛很不愿意与智力如此低下的人多说什么,“朴彦成一家,原是高丽顺王的人,王运做了高丽国王后,顺王一些旧党,逃到了辽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人在高丽国内,亦并非全无势力。朝廷为万全计,令朴彦成出使辽国,目的便是暗中接近这些人,并设法分化他们,操纵他们。若要将柴远荐给辽国君臣,上策便是通过这些高丽人。”
范翔这才放下心来,他没有再问朴彦成身边为何没有职方馆的人监视——毫无疑问,朴彦成一定在职方馆也有份薪俸。但他心里面又冒出一个疑问来……“你到了辽国,要谨防辽国通事局。”潘照临没有容他再多问,回头瞥了柴远一眼,便出了亭子,上马离去。范翔看了看柴远,又看了看潘照临的背影,终于忍不住,苦笑出来。
将柴远介绍给范翔之后,潘照临便策马往陈桥门回城。此时,陈桥门前,依然是一片肃穆之色。把守城门的兵吏都戴着孝,数量却比平日多了一倍还不止,对出入城门的人,盘查亦十分严格。潘照临不由得摇了摇头,轻轻叹了气。在往年这个时候,因为是灯节,便是各外城门上,也会张灯结彩,但今年的灯节,却早已名不副实了。
先皇帝赵顼升遐,举国同哀,开封府在天子脚下,自然更不能马虎,汴京城昨日便已经满城戴孝——这些对汴京百姓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二十余年间,算上赵顼,许多百姓已经经历了三个皇帝的去世。真正令得整个汴京如临大敌,百姓惶恐不安的,是八日晚上的石得一之乱。
当晚的变乱,前后不过两个时辰就被平定,对坊市也未造成很大的损害,事变之时,除了内城与新城城北的一些居民有所察觉,大部分市民都一无所知。然而,在叛乱平定后,它波及的范围,却让汴京城数以千户的人家都忐忑难安。石得一等主谋,的确皆已死于平乱之中,但涉及叛乱的却包括整个皇城司和部分班直。这些人,尤其是皇城司兵吏,多数都是开封本地人!
陈桥门前的兵吏,便是在搜捕参与叛乱的漏网之鱼。
便是昨日,亦即九日清晨,首相司马光在福宁殿灵前宣读先帝遗制,太子继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朱妃为皇太妃。紧接着,便又下令,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以仁多保忠、杨士芳、田烈武守宿福宁殿外,另又分遣武臣增兵防守军器库,以及宫城、内城、外城诸门,并暂时令李向安等内侍,接管皇城司事务。
自大宋立国以来,新帝即位,增兵宿卫,这是“祖宗故事”。但特意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却是不同寻常——因为按照礼仪,臣子前往福宁殿,宰臣和百官是走垂拱门,而亲王宗室则是走内东门!
潘照临知道这燕达亦算是熙宁朝名将,他西军出身,在熙宁初年与西夏、西蕃的战争,曾经屡立奇勋,但因为赵顼认为他忠实可信,从军制改革起,便将他调任三衙,从此便一直在京师,他没能赶上伐夏之役,自熙宁中后期起,于战功上反而并不显赫了,但此公仕途上却一帆风顺,竟一直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乃是大行皇帝的亲信,在军中又素有威信,令他宿卫内东门之外,其意自是在于警告诸亲王宗室。
而在皇宫之外,韩忠彦则在按图索骥,分头搜捕参与叛乱的兵吏,命令各军巡铺盯紧他们的家属——连大赦天下也救不了他们,潘照临已经看到了今日上午颁布的大赦天下的德音,这道德音上明明白白写着:除谋逆罪外!
想到这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雍王赵颢。
石得一、石从荣等人,被视为“主谋”,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那些可能只是盲从,或者被胁从的皇城司兵吏,亦被四处搜捕。但如何处置雍王,却变成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擅出王府这一条罪状难以洗脱外,参加叛乱的头领,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搜查这些人的宅第,都是韩忠彦主持,事后汇报,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而与此同时,咸宜坊雍王府的“安全”,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御龙骨朵直负责,为了防止雍王自杀,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几个高太后亲信的内侍,昼夜不离的陪着赵颢……这种种迹象表明,朝中存在着强大的势力,想要保全雍王的性命。
个中原因潘照临都懒得去想,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三五十个来,为皇家的体面也罢,为了朝廷的面子也罢,为了高太后也罢……总之,雍王虽然被禁锢,但明正典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否会赐赵颢自尽,亦不可知,韩忠彦就私下里对石越说过,雍王纵然有过,然使高太后杀子、赵煦杀叔,亦非忠臣所为。
而韩忠彦的这种主张,亦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何况,朝中人人都知雍王是高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今高太后垂帘,即使是明白内情的重臣,也不免各有算计。韩忠彦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他先父又是两朝策立功臣韩琦,才敢不避嫌讳。饶是如此,韩忠彦这几日的举动,已是令得满朝文武刮目相看,连潘照临与石越都感到惊叹。
但旁人便不可能没有顾忌。
想要置赵颢于死地,将来高太后那里肯定不会怎么被待见;但若只顾着讨了高太后的欢心,甚至哪怕纯粹只是一片忠心,若无韩忠彦那等家世、功勋,向皇后与小皇帝现时固然不敢违逆高太后,难道高太后就会长命百岁?待到小皇帝长大亲政,难保不会秋后算账。他现时忍得越久,将来报复起来就会越狠!
潘照临不由得又在心里面算计起来:
赵顼虽死,但两府当中还是有忠于他的宰执。侍中王安石、兵相孙固,二人皆受赵顼知遇之恩,年纪也大了,名位已高,再无所求,亦不惧得罪高太后,故对于赵颢叛乱之事,心怀耿耿,绝不肯善罢甘休。只不过二人并无证据,不能就此发难而已。而除韩忠彦外,范纯仁、御史中丞刘挚,却都有意保全赵颢的性命。
其余诸人,司马光虽态度不明,但潘照临却认定他亦不想对赵颢赶尽杀绝。而且他是首相,按例要担任山陵使,诏令在大敛成服前就会颁布,所以他有足够的借口谋定而后动。
而吏部尚书王珪虽然平叛无功,却因为进宫时被石得一禁锢,受了惊吓,竟然就此一病不起。赵顼选定的六位托孤之臣,眼见着他刚刚升遐,便要少了一位。王珪一生行事,本来就无甚主见,此时更不会强出头。
至于韩维、苏辙、李清臣三人,韩维在理智上纵想饶过赵颢,但他毕竟是赵顼潜邸之臣,对赵颢之愤恨,可想而知;苏辙心里便有想法,但此事既无关他利害,又无情感之羁绊,他回京未久,地位未固,此时惟石越马首是瞻,亦不奇怪;而李清臣虽是后进,然受赵顼之知遇恩,不在韩、孙之下,只是在两府宰执之中,他的地位最不巩固——他虽然支持新法,却与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并无故旧,而是由赵顼一手提拨,赵顼一死,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无援,而偏偏他在太府寺的政绩还受人诟病,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势下,以李清臣的性格,定会加倍谨慎,远避是非。
朝中重臣各怀心思,因此,在此事上,石越的态度犹当谨慎。
石越贵为右相,又是托孤之臣,在朝中本就威信素着,此番平叛,又立大功,他一言一行,都已是举足轻重。更何况此番王、马意见竟然出现分歧!
虽然,在这些事上面,连潘照临也弄不清石越的态度究竟如何……但潘照临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替石越事先谋划好这一切。
但是,当潘照临回到石府之时,石越却正在病榻上接见桑充国与吴从龙、曹友闻。
这吴从龙原亦是陈良的旧识,最精于礼制典章之学,早就投入石越门下。但他自入仕以来,因吏材平庸,又受石越牵累,竟徘徊州县十余年,一直难以升迁。直到石越重掌权柄,陈良在石越那里帮他说话,这才终于让石越想起还有他这么个人,将他调任鸿胪寺主簿。他三日前方抵京履新,正好避开了国丧。
潘照临亦不知道这三人如何竟会凑到一块,但石越八日晚上在福宁殿指挥平叛,左臂受伤,九日又忙了一天,没心思去管这伤情,不料到了九日晚上,竟突然晕倒在回府的路上。宫里派了太医来诊治,特许石越休养一日,便这么一日之闲,石越却又会见起桑充国等“闲人”来。潘照临又见陈良与侍剑不加阻止,反在一旁作陪,言笑宴宴,心里更加不悦,撇了撇嘴巴,走到石越榻边,亦不说话,自己挑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众人见他进来,除石越外,连忙都起身行礼。石越却没留意潘照临的脸色不对,只是微微颔首,便又转头对桑充国等人说道:“潘先生亦是自己人,不必拘礼。长卿,你继续说南北之论,亦让潘先生评点评点……”
桑充国点点头,又向潘照临以目示意,道:“我刚刚听曹员外说起两浙人才之盛,便想到前些天几个福建学生的南北之论……此事却要从本朝进士第说起,因今年是省试之年,学院里,有好事之人,贴了一张大表出来,上面列举了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