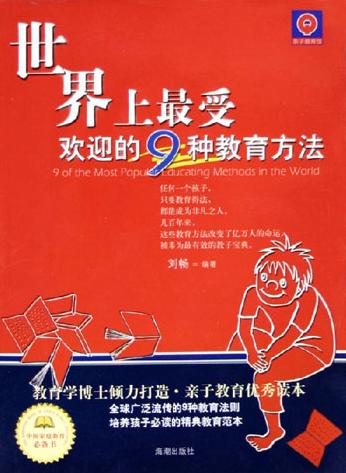动荡的九月 [苏] 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不,男女私情是不可能的。只有成年的单身婆娘,因为家里没有男劳力、生活实在困难,才会拉格纳特去试试。
“还背来了一袋子嫁妆,”瓦尔娃拉继续说。她把补好的棉袄扔给了格纳特。“好了,小女婿,回家去吧……我可怜他,”她对我解释道。“格卢哈雷村里的人喜欢空发议论,可是没一个人肯做好事……行了,走吧,格纳特!”
他急忙扣棉袄扣子。瓦尔娃拉把一块黑麦面包头塞到他的怀里,又替他扣住了扣子。
“等一等”说罢,我走到袋子跟前。
克罗特没有说谎。格纳特确实常到防区去。根据袋子鼓出来的形状,我猜到这个痴子背回来的是几个完整的炮弹。大概,他在树林里无法把铜衬套凿下来吧。
我把袋子里的东西一下抖了出来,里面有小锤子,凿子,两打弯曲的铜衬套,最后还有三枚七十六毫米大炮的炮弹。雷管都在原来的位子上,有一只雷管的杜拉铝护罩也掉了,振动片都能看得到。只要跳蚤对准振动片打一个喷嚏,瓦尔娃拉这些壁毯就会飞到老爷府的遗址去。这个袋子,格纳特是怎么背的呢?憨人真是有憨人的运气呀!
“给我一把平嘴钳,”我对瓦尔娃拉说。
她把工具拿来。
“有个真正的男人在家里,该多好呀,”瓦尔娃拉笑盈盈地看着我,毫无惧色地说。“就有人卸炮弹的雷管啦!”
我小心翼翼地拧开了弹头。
“你别再干这活儿啦!”我对痴子说。“别再干啦!别用袋子背了!”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也许,炮弹在他的眼里是小猪崽吧?他是在树林里放猪崽的,把最听话的背回家来,背到自己那间歪歪斜斜的小木屋去。铜圈圈是枷锁,他要砸开小猪崽颈上的枷锁,让他们自由自在地……
“他一直到防区去。为克罗特卖命,懂吗?”我对瓦尔娃拉说。
她举起双手,拍了一下说:“他不怕土匪吗?”
格纳特还在笑。真的,他背的是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炮弹,那土匪对他来说还算得了什么呢?
“喂,格纳特,”我心里暗暗抱着一丝希望,“你在那边,在树林里,碰到过什么人没有?背自动枪的?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他高兴地学着说。“哒、哒、哒、哒!好吃!面包!脂油!好,好吃,马—马斯科的甜脂油!”
“还有什么脂油?”我问。
“那边,”他往窗子的方向一挥手“好吃!”
“好了,够啦!去吧,痴子!”瓦尔娃拉把格纳特那顶帽子低低地扣到他那蓬乱的头发上,把他推出门外。
她飘然走进屏风后面的卧室,不多时,她穿着一件城里人穿的绉绸短上衣和一条百褶裙走了出来。
“怎么样?”瓦尔娃拉问道。“漂亮吗?这东西是我换来的,可多哩!从城里人那儿换来的!他们日子挺难,穷得牙齿都闭起来了。可咱们是庄稼人,咱们可以从土里刨食。”
她两手一抖,一块浆过的雪白桌布仿佛自动地铺到了桌面上。桌上出现了一个女人想请男人吃一顿他终生难忘的佳肴。如果杜鲍夫和那帮小伙子看到这桌酒菜,准会目瞪口呆……
“我琢磨呀,你不会来了呐,”瓦尔娃拉说。“永远也不会再来!你怕难为情吧?怪人!眼下您还不够男子汉的格儿,倒先变成了好斗的武夫。我看,您在战场上打死的人不止一个了吧?”
我一声没吭。
“嗨,你瞧你!”瓦尔娃拉说。“见了女人还害臊呐!哎哟哟……”
她的乳房在绉绸上衣里显得轮廊分明。一双眼睛呈现出李子般的墨绿色。这个颜色,噢,见鬼,我的脑子里又出现了树林,又出现了当你走在小径上,看到秋播田在九月秋阳照耀下显得一片葱绿时的情景。那时你可以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既不受回忆时内心羞愧的约束,也不受爱情的义务约束。我的眼前又闪过了一个裹黑披巾的姑娘的模糊形象,这个自由、秀丽的形象是属于树林、田野等大自然的。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姑娘挑着担子,走路为什么那样稳重、那样优美。造物主完美地创造了她,她象一茎草,象一株秋播的麦苗儿。
我坐在瓦尔娃拉的身边,可我脑子里想的却不是她。
“坐嘛!”我说。
她立刻坐了下来。她身上既有一种并不让人厌烦的、又能缠住人的威严,可也有随时准备服从的性格,真叫人诧异。
“你同火烧鬼有过那种事?”
“原来是为这个呀……小傻瓜,这难道有什么要紧?”
“要紧!我就是为这来的,懂吗?”
“啊,是这样……”她闭紧嘴唇,沉思起来。
“火烧鬼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活动,”我说。“就是他把什捷勃列诺克吊死的。”
“他不会吊死你的。你干吗这么着急?”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吊死我呢?”
“我知道。是的,我同他有过那种事!”她从桌子上探过身,凑到我面前说。她的胸脯压在桌布上,绉绸跟桌布碰在一起,融合成一种颜色。“你照我说的去做,他就不会碰你。现在他不会冒这个险了,不是那个时候了。冬天一到,他得远走高飞了!”
她的话有道理……到了冬天,野兽也好,人也好,都会被自己的足迹暴露出来,他不敢再在村子周围转悠了。
“下雪之前,他还能干不少坏事呀!”我说。“他是恶棍,他是法西斯分子,班德拉匪帮嘛!”
“你才二十岁,凡尼亚。你要珍惜自己,还有多少姑娘会来爱你呢!”
“你看中他哪一点呢?”我打断她的话头。
“我应该看中他什么呢!”她用豁达的口吻说,仿佛她是在跟一个不懂事的、爱问这问那的孩子在说话一样。“我不必看中什么……他想要娶媳妇。他是个男子汉!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甚至挺魁梧。打仗的年月里,这样的人多吗?”
“德国鬼子走了后,你仍旧同他见面?”
“亏你问得出口!傻瓜才回答你这个问题呐!”
“是不是你给火烧鬼送吃的?给他洗衬衫?
“我?……”她纵声笑了起来。“我给他洗衣服?你太不了解我了……”
“这是实话?”
“我可以对天发誓!”
“火烧鬼会到村子里来看你吗?”
“我怎么知道?”
“如果你叫他来呢?大概你知道对谁悄悄说一声,他就会来的,是吗?”
“他自个儿并不想来。他身边可带着宁卡·谢麦连科娃啊!带的不是我,是宁卡!他俩看样子不是逢场作戏!”
是啊,我穿起挂满奖章的新军装,竟以为自己能够巧妙地,得心应手地利用女人家的幼稚心理,我太过于自负了。瓦尔娃拉对我不承担任何义务……
“谢麦连科娃的情况,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我问。
“嗨,这种事儿,我们女人家想知道都能打听来。您,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干吗需要追根问底呢?”她又卖弄风情地用“您”相称了,“今儿个晚上多美呀?您要么为火烧鬼的事逮捕我,要么就别再问啦!”
她凑到我的身边,我的脸颊上感到她呼出的一股股热气。她身上散发出香肥皂的味儿,不过在一千九百四十四年,格卢哈雷村里会有什么香肥皂呢?
“我不会逮捕你的。”我愁眉不展地说。
两个人的眼睛对视着。我仿佛就要飞也似地向她扑过去,两个人马上就撞在一起,撞得粉碎。
“听我说!”我央求起来。“他从前大概爱过你。他一定还会想见你……你能帮我一把吗?叫他到村里来,行吗?”
“不行,”说罢,她的身子又挪开了一些。“我不想叫自己……也不想叫你去找死。这样干不行,为点啥要把自己的命送掉?”
“那怎么做才行呢?”
“听我说,”她用自己的手掌盖在我的手掌上。她的手滚热,象暖手袋一样。我小心地抽出手来。“搬到我家来吧。就算招女婿……来不来由你的便!你来,会有好日子过的,我来张罗你……你是伤员嘛,你要有一个好心肠的女人,一个体贴、温柔的女人……给你弄吃,给你弄喝,我对你永远不变心!真的!我们女人可不是因为贪图什么才找男人的。我会爱护你的!”
“那火烧鬼呢?”我问道。
“什么火烧鬼?我可没有调查你的历史。”
“这样做他会高兴吗?”
“让他不高兴好了,”瓦尔娃拉声色俱厉地说。“要不,咱俩一走了事……跟我在一起,你不会有闪失的,你可以挨到打完仗。你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应该考虑考虑自己啦。我虽说不象你那样有文化,可我的头脑还是挺灵光的。我说的都是正经话.凡尼亚……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兴许,她说的是正经话。是个明智的主意:吃饱穿暖,美美地过日子,一直到仗打完。可同志们在前线,大概又得匍匐着爬到前沿那一边.回来后一点名,照例又要少几个人。
“不行,瓦尔娃拉.”我说。“这样的生活我消受不了。如果这话是出于真心,我表示感谢。”
“你不怜悯我?”她问道。
“眼下顾不上这个,”我没有看她,身子往边上挪了挪,说。“土匪就在村外。怜悯你,……怜悯自己,那就毁了大家!”
“唉,傻瓜!”瓦尔娃拉说。“你不知道你的命值钱?你比别人金贵得多!哎,这你怎么不懂呢?你呀,应该知道,虽说你打过仗,可是在火烧鬼面前大不了是根胡萝卜。你应该听话:我劝你还是逃命要紧,避避风吧!”
“不行,瓦尔娃拉。我不能走这条路……”
“你也断了我的路,”她说。“伊凡,你给我只留下一条……”她突然打住了。“我想靠你遮风挡雨,懂吗。你可以救出我,我也可以救出你。咱俩一报还一报!”
“那好啊!”我按捺不住了。“好!先帮我收拾火烧鬼。你说,怎样才能逮住他!”
“要我断送自己?那我干吗要卖力气呢?不行!”瓦尔娃拉口气坚定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你想逮捕我。你就逮捕吧!”
“好,我走了,”说罢,我站了起来。
得赶快离开这儿,赶快跑!
“你到底是个毛孩子,”她结结巴巴地说。“他们给你挂这么多奖章,可你还是个毛孩子!你想当英雄?你没看见缺胳膊少腿的英雄有多少?谁需要他们呢?而那些躺在地下的呢?……”
正在这个当儿,前室里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波佩连科敲了敲门,也不等主人应声,就闯进屋里来了。我看见是他来了,别说有多高兴!
他一眼看清了屋里的态势,目光朝桌子上一瞟,瞧见桌上的酒菜还没动,立刻喜上眉梢。
“咱一直在找你!”他对我说。“今天是伊凡斋戒日嘛!不给首长贺个节可不行!”
他抓紧时间,脱去外套.把自己的马枪往角落里一戳,解下子弹带。我这位部下向来是不讲究客气的。如果说有什么现在使他发急的话,那就是瓦尔娃拉那对泪汪汪、充满怒火的眼睛。
“甭伤心,心肝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