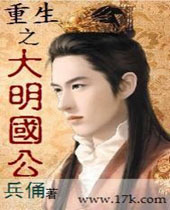重启大明-第6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丁一许下的诺言,就更有信心。他是回到船舱里之后,想清楚了这一点。
相对来说,海上的航程,单调而孤燥。以至于他们还有心思,为着莫蕾娜的肚子而生出纠结来。
丁一却就没有这样的心思了。
因为他正在听取着随补给舰队而来的挞马赤伊基拉塔的汇报。
主要就是对于现驻在乌思藏的大明第一师的一些情况。
挞马赤伊基拉塔现在的大明官话已说得很流利:“好教那颜知道,原本从云贵入藏的路线。试了之后,小股精兵或还有可能,大明第一师这样携带大量装备、弹药、辎重的大部队根本就难以成行的。”
“是我记差了。”丁一点了头,向挞马赤伊基拉塔问道。“从昌都那边过去?”
“那颜明见万里!”挞马赤伊基拉塔谄媚地奉迎。大明第一师最后是从金沙江。也就是昌都那边进入西藏,期间又是建兵站,又是征发民夫修路,一路去到正统二十年的年尾,丁如玉才领着大明第一师进入了乌思藏地区。
丁一持着地图,向其道:“如玉驻在此处?”他所指的是拉萨区域。
挞马赤伊基拉塔摇了摇头道:“丁总镇带着随身的亲卫,率第一旅驻在山南地区。”
石璞因为年纪大,就把总督行辕放在了拉萨左近。而胡山的大明第一师师部,就也放在拉萨。
而作为丁一所部的烙印。加上要征发民夫等事,一驻扎下来,自然就是工宣队四出,去各个聚居点里宣讲人生而平自由,贫穷和苦难都是奴隶主的剥削。出乎意料的是,在乌思藏地区,诉苦大会的反应,要比在两广等地差很多。
不是藏地的民众日子幸福,而是他们麻木了。
这年代,乌思藏行的就是比西欧中世纪更为黑暗和残忍的农奴制度。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黑暗和残忍,不单是乌思藏地界把人按血统贵贱和身份高低,划分为三等九级。然后杀人不用偿命,《杀人命价律》就是按照这些等级对赔偿命价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有钱人和贵族杀了人,扔点钱就是,占人口总数超过九成的穷人真是想要申冤都没处去。
“这比原本草原上的贵人还凶残。”挞马赤伊基塔说着不住摇头。
丁一无语地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他知道这是实情,不单是杀人命价律,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
也就是他们从出生就欠债了,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当然他们可逃跑,但捉住了会被罚下高额的罚款,于是更加还不清债务;就算逃跑成功,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所以面对工宣队的煽动,农奴们压根就生不起什么反抗的激情,他们怕了,麻木了。
以乌思藏的民歌来说:“山上有没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主的人。”
可见,惨到什么地步?比山上的野兽都不如,至少野兽还有点自由。
“那颜,我却是背着案子在身上的,胡师座把小人这队人打出过来出海,是他保全不了小人,只能来求那颜的庇护!”这挞马赤伊基拉塔,说着便跪了下去,“不是我故意有心隐瞒,实在是寻不着机会把这事禀报。”
要见丁一,现在也不那么容易,不见得丁一端起架子,他总归千头万绪都要他去做决定。如果不是丁一在船上,恰好看到这厮在指导那些山地特种大队的士兵开弓,叫他过来说话,也许再过二个月,也不见得能见着丁一。
丁一倒也没有动怒,示意曹吉祥把茶斟上,便对跪着的挞马赤伊基拉塔说道:“说来听听。”
总归是智慧生命,在工宣队一次次的宣讲,一回回地引导之下,农奴之中,还是开始有了觉醒的人。
而那些领主、宗本、寺院里总管,也觉察出不对来了。
他们开始认为,请明军入藏,是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于是这些地方豪强,开始扑灭火种。
别问农奴是不是傻了?被欺压得这么惨,还替领主卖命,去攻击来替他们说话的工宣队。
他们没有知识,这种黑暗的制度,原本历史上是到了新中国,才开始被取缔的。也就是说,上千年来都是这么过的,他们也习惯了。
在拉萨地区开始工作的一支工宣队,就这么被领主包围了。
“他们要制止一个领主的管家,喝了酒无故来殴打农奴的行为。便惹了祸!”
挞马赤伊基拉塔是随着边患起,丁如玉带兵入乌思藏时,关外支援过来的部队走的,他在关外依附着丁如玉和陈三,渐渐地倒也历练了出来,虽然依旧麻杆一般的身段,却褪尽了原本那一身的猥琐气味,当时在胡山麾下充任师直属警卫营的骑兵连长。
那日胡山派人去召他入内,他给胡山行了礼,还没开口,胡山就把那份密码军报递了给他看。挞马赤伊基拉塔对丁一说道:“那报告上的密码译出来,便是这么几句话:我们只有两把左轮二十四发子弹和四柄手榴弹,请师部尽快派人过来,对方有至少五百人。”
丁一听着头疼,抬手揉了揉太阳穴,两把左轮和四颗手榴弹,济得了什么事?
再说不能否认的就是,工宣队的军事素质,通常来说,不是很拔尖。
“胡山让你去接应他们么?”丁一冲着挞马赤伊基拉塔问道。
后者摇了摇头:“胡师座来问我,说是前日上报西南有马匪横行的事,可是属实?”
他何曾上报过这样的事?再说他是师直的警卫营骑兵连长,他的职责也不是去充当侦察部队啊。不过原本在关外能当上部落小汗的赤军长胜,脑子却是灵活的,他笑着对丁一说道:“胡师座是那颜的弟子,他这么问,我听着也是知机,便答道是,前日去接那批新兵,听着那些‘堆穷’述说,说是少了几头羊,只怕是被西南的马匪杀了。”堆穷就是农奴制度下,最下层的民众。
丁一听着禁不住点了点头,对他道:“起来,坐着好好答话吧。”
他敢在丁一面前,把话说白,便是以丁一亲信自居了,丁一当然也不会拒人千里之外。
“谢那颜!胡师座教我带领骑兵连去,查一查此事是否确实,又说先前派出工宣队也在西南,教我也把他们接了回来。还说是,若遇见马匪,不受降。”不受降就是不留活口了。
丁一当然听得懂这意思,就是胡山教挞马赤伊基拉塔,把那敢向工宣队动手的领主杀尽了去,这一点丁某人倒是无异议的,点头道:“胡山难得硬气,这事却就应如此料理!”
“好教那颜知道,却不是胡师座硬气,是这事若给总督辕门知道,只怕胡师座要吃排头,我等都没一人能活!”挞马赤伊基拉塔极为无奈地长叹着说道。
丁一听着眼神一冷:“石某人管到大明第一师头上来?”
这绝对不是丁一能接受的事情,他很清楚石某人这些士大夫阶层,对于战士是什么态度。
而且在立宪没有推行,军队国家化的进程没有开始实施时,丁某人怎么可能把自己手上的军队任人插手?
第七章狰狞(六)
挞马赤伊基拉塔苦笑着摇了摇头对丁一说道:“其实那场祸事,依着我来看的话,便是石总制惹来的火头!”他这话不算冤枉石璞,至少石某人的态度就是引发起此事的导火索,因为在经之的一些日子,有名士兵在行辕附近制止了一个领主对农奴的非礼,结果那领主就吃了一枪托,这事最后闹到总督行辕去,石璞居然叫亲兵打了那名士兵两耳,然后把士兵和那小领主一起轰走了。
甚至之后还找胡山过去,训斥了一顿,说是:“边患起,正当安抚僧官、豪强之心……尔当约束军士,不得无事生非!”对于石璞来说,军兵虽然和农奴有些区别,但都是属于可以被牺牲的代价,至少,为了安抚当地豪强,他决不会为了几个工宣队工作人员的性命,去跟当地领主翻脸的。
丁一听着微笑起来,点头笑道:“石总制果然是着眼大局啊。”曹吉祥在边上听着,却觉得石璞只怕要坏事,他很清楚,丁一此时是起了杀意的。
挞马赤伊基拉塔老老实实地接着禀报:“胡师座对着我说,这马匪只怕是一时半会剿不完的,教我再去骑兵旅,调多一连人,和骑兵连一道,把马匪好好清剿一番,以免得他们为祸乌斯藏。胡师座又说,这马匪专门劫杀领主和活佛,这样是很不好的。小人依命去了,调的便全是都音部落出身的人马。”
丁一听着对文胖子说道:“给胡山记一功。”
“是。”文胖子取了本子出来,做了记录。他现时不单是相当于警卫队长,还充任着丁一副官的职能。
丁一当然知道,明显胡山是在安排挞马赤伊基拉塔去干黑活。
不单要把那支工宣队救出来。而且接下来他还要扮演马匪的角色,把那些敢于和大明第一师明面上作对的活佛、豪强,都统统劫杀了才是。
不过挞马赤伊基拉塔不介意充当这样的角色,也当过小汗的他很清楚,这就是自己成为心腹的开始,他不是一个甘心当一辈子连长的角色。
“当时有个农奴,是工宣队长托他出来送信的。在边上流着泪说,工宣队完了,一定完了。他家里也完了,他出来时,在路上看着管家老爷,又领了几百人过去。这样加上先前那几百人。就有千人上下的光景。我领了兵去时,确是这般上下。”
丁一把曹吉祥斟好的茶,取了一杯放在挞马赤伊基拉塔的面前,示意他喝口茶:“慢慢说,不急。”的确不用急,他们在船上,此时的海风也让他们不可能回航。当然,三角帆可以走之字形。但耗费的时间要远远比顺风久得多,所以。真的是有足够多的时间。
挞马赤伊基拉塔很小心地喝了一口茶,对于在关外长大的他来说,茶砖都是很珍贵的物件,更别说丁一喝的茶叶:“我当时也是没法子了,这出得去,不知道啥时回来。便跟那些兄弟说了实话,这回出去,是要去当马匪的了。大伙都当了兵,有身份的人了,便都不肯去,我便告诉他们,是那颜的弟子下的令,大伙说,那颜弟子的令,那就得听,便领着出了营去。”
都音部落和关外出身的这些士兵,要说觉悟多高真的是没有,只不过他们对于丁一有着一种狂热的崇拜,和近乎偏执的信赖,然后爱屋及乌漫延到胡山的身上去。不单单因为丁一是强者,是生俘了脱脱不花、也先等人的强者,更为重要的是,丁一就是一个传说,草原上的传说。
“这些不用废话。”丁一听着笑了起来,抬手对挞马赤伊基拉塔摆了摆,说道,“说正事。”
“是,在路上,我们便遇着第二个来送信的农奴,他是走着出来的,一身的泥和牛粪,臭得不得了,我们在关外也苦,都不曾这模样。”挞马赤伊基拉塔陷入了回忆之中,他的语气,渐渐地带起很沉重的伤感,就算是已经历过的事情,依然教他觉得难以承受的痛。
丁一自己动手给他斟满了茶,对他说道,“这封信,有问题?”
“是,这信是工宣队的弟兄,被逼写的。”挞马赤伊基拉塔的脸上有止不住的痛苦。
那封信,挞马赤伊基拉塔还保存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来,小心翼翼,象是拿出一块价值连城的珍宝,打开包裹着的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