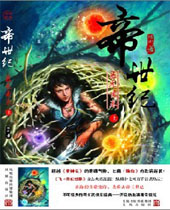半个世纪的改革变迁:世道-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能三点上烟袋抽着,感慨地说:“看不出你爹的思想还挺开通呢。这一合营,你爷爷留下的那点家产,可就都完了!”
“爹,听说咱村成立了高级社,是吧?”
张文然贸然地问了这么一句。李能三说:“高级了,全村都高级了。我连初级也不初级。”
“咱家还没入社呀!”
张文然故意惊讶了一句。李能三对女婿的责备很不满意,不禁皱起了眉头,“我不入社怎么啦?这又不犯法!只要不强行命令,我就不入。”
张文然见老丈人变了脸,便觉得自己说话有些冒失。为了讨得老丈人欢心,装出一副笑脸说:“其实,城里的公私合营,也是强调自愿,共产党不搞强迫……”
“不搞强迫?说是这么说,做起来就不是这样了。”李能三说,“他们今天给你做工作,明天找你谈话,后天又叫你开会学习,这不是强迫是什么!”
李能三发泄着不满。张文然心里直笑:城里实行公私合营,岂不一样!这是潮流,必须顺着走。明明心里不同意,脸上还得挂着笑。他想给老丈人做做工作,又觉着自己没那么大本事,只是试探试探而已。他说:“城里的工商户都敲锣打鼓地到县委去报喜,看样子挺高兴的。”
“你爹真通了?”李能三自问自答地说,“我就不信。把自己的家产拱手给了公家,心里还高兴?这不傻了!”
张文然趁机说:“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共产党嘛就是搞共产的。今天你不入社可以,明天不入也可以,可总有一天就不可以了。”
“我就不信他们会把我怎么样!”李能三倔倔地大声说着,狠狠地在鞋底上磕着烟袋锅子。
青茶娘把饭端上来,见爹在粗门大嗓地喊叫,嗔怪道:“这是为啥呀,怎么一见面就吵?快吃饭吧。”
李能三见老伴儿炒了鸡蛋,切了香肠,便说:“今天孩子们来了,高兴。来,我跟文然喝两盅。”说着,就去拿酒。往日他自己喝的是散酒,今天特意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老白干。
翁婿俩慢慢喝着,青茶与陪娘在屋里说悄悄话。李能三听青茶说公爹因为合营的事住了院,就说:“抽空我进城去看看他。”
“没什么大病,出院了。”文然想,爹现在思想通了,兴许能给他做做工作,就说,“俺爹叫你去呢。”
“我也想他了!来,喝酒。”李能三高兴地举起酒杯……
又是一个大旱之年。冬天没下一丝雪,春天没下一滴雨。地里干透了,庄稼打了蔫,叶子拧成了绳。县里召开紧急电话会,号召农业社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多打土井。然而,农业社并没有因为转成高级社,就立马富裕起来。虽然取消了土地分红,实现了集体所有制,家底依然很穷。区政府分给东堤村打二十眼大眼井的任务,石大夯感到压力很大。他赤手攥空拳,纵有十八般武艺也打不出这些井来。高级社用工不发愁。木料呢?砖和水泥呢?这些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他粗略算了一下,少说也得三万砖、两方木头。这些东西到哪去弄?这事压得他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
李碾子当干部锻炼得能说会道了,还肯出主意想办法,成了大夯的得力助手。他知道大夯为什么发愁,故意跟他开玩笑:“如今咱村已经是高级社了。在全县是蝎子的巴巴——独毒)一份粪)。你光彩,我光彩,咱村的人都光彩。区里、县里表扬咱,外村学习咱,你愁啥?……”
石大夯苦笑笑说:“碾子,你别给我烧高香、戴高帽了。现在咱们不是唱蟠桃会,而是过火焰山。眼下区里催打井跟逼命似的,你快给出个主意啊!“
“这并不难啊!”李碾子不以为然地说,“大夯我问你,如今咱这社是高级社不?”
“是啊。”
“高级社与初级社有什么不同?”
“取消了土地分红,消灭了私有制。”
“这不得了!”李碾子摇头晃脑、得意忘形地说,“既然是公有制了,这社里所有的土地、牲口、农具,一切的一切,全归咱支配对不?”
石大夯着急地说:“你想说什么呀!”
“咱们实现了公有制,打井需要什么,你尽管说话就是了。”
大夯仍感到云山雾罩:“咱这社刚成立,要啥没啥呀!”
“不会跟社员们要嘛。”
“跟社员要?”大夯还是不明白。
“对呀。”李碾子高兴地说,“成了高级社,全村就成了一家子,有难事也不能你一个人发愁呀!区里不是叫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吗?这钱、这砖、这木头,都叫大伙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刚解放没几年,社员们没什么家底。”
“别看有人喊穷,家底沉实着呢,有潜力可挖!”
石大夯眉头一皱:“挖潜力?”
“你成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事到临头,怎么忘了这条基本原理呢?”李碾子说,“社是大伙的。克服困难,就得靠大家。我看不妨开个会,把上级给咱村的打井任务告诉大伙,把困难也说给大家。来它个有钱的出钱,有砖的出砖,有木头的出木头,困难不就解决了?”
韩天寿说:“碾子这主意好,咱们就让社员们摊!”
石大夯摇摇头,“现在人们还不富裕,怎么能向社员们伸手哩!”
李碾子说:“要说富裕,多数户并不富裕。要挖潜力,谁家也有潜力可挖。就当是社里借社员们的,记上帐,以后再还嘛。”
韩天寿接腔说:“反正都是社里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什么呀!”
“借比摊派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大夯想了想说, “咱开个会商量商量吧。”
第二天一早,石大夯就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所谓代表,就是每户来一个当家主事的。大夯把区里给的任务,打井所需要的资金、木料、砖和水泥,全亮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尽管李碾子一再给大家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大伙儿还是老牛戴笼头——不张嘴。大夯说:“咱村已经是高级社了,高级社就得显出高级社的优越性,就得增产。要想增产,必须解决抗旱问题。咱们村虽然紧靠黑龙河,天一旱也指望不上。我们不能靠天吃饭,必须打井。打井就需要钱,需要砖和木料。想让大伙儿挖挖潜力,支持支持。把那些暂时用不着的砖和木料借给社里,秋后再还。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伙儿凑一凑,问题就解决了。”
大夯的话刚落,韩天寿就抢嘴说:“眼下消灭了私有制,就把家里的东西献给社里吧。”
“怎么能这么说呢!”石大夯低声责备了韩天寿一句。解释说,“这次打井是社里借大伙的,秋后一定还。”
李碾子也给大夯助威:“社是大伙儿的,社里有困难,大伙儿就得帮忙。”
韩一强冲碾子撇撇嘴说:“碾子,你家有钱就借给社里打井吧。”
这一问把李碾子的嘴堵住了,他家确实没有钱,说话也就不仗义了。
“漂亮话谁也会说,关键要看行动。”韩六子鄙夷地瞥了碾子一眼,“我说副社长,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这是在将李碾子的军。石老大对韩一强和韩六子特别反感,“一强和六子,别光将别人的军,你们家有力量,就支持支持社里打井。”
“我可没什么潜力。”韩一强赶紧推辞,“现在土地不分红了,都靠工分吃饭,我挣的工分并不多。”
韩一强这么一说,人们挺烦他。李根大说:“前两年初级社的时候,你仗着地多,沾光可不少啊!”
“我说李根大,我入社吃大亏了,可没沾什么光!我要像李能三那样顶着不入,胶皮大车早就栓上了。”
老鼠四顶他一句:“一强,你甭在这里卖冤,要觉着不上算可以退呀!”
韩一强说:“杨书记叫退吗?”
“净说些离板儿的话。”石大夯见人们扯远了,赶紧把话题拉回来,“为了抗旱打井,大家就各尽所能吧。打井是为了增产,让社员们多分点。这事得靠大家。我再强调,这东西不是入社,是借大伙儿的。秋后马上还,要东西给东西,要钱折成钱。”
人们还是沉默不语,石老大为大夯捏着一把汗。他心里燃着一把火,霍地站起来说:“我献副棺材板!”
大夯见爹要献棺材板,不由地一愣。这副棺材板是爹的心爱之物。再说爹的肝病直犯,咋能用它打井呢!他瞅了爹一眼,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爹知道大夯担心什么,便说:“我这把老骨头眼下还趴不下,那副材板一时半晌还用不着,让社里救急吧。”
人们都向这位干瘦、佝偻的老头投来敬佩的眼光,有人竟鼓起掌来。
四唾沫说:“这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哩。打井就得靠大伙儿……”四吐沫满嘴喷着唾沫星子,拉开了话匣子。人们怕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便打断他的话问:“四吐沫,你拿钱还是拿东西?”
“我家啥样大伙儿都清楚。钱我拿不出来,家里还有几百砖,拉去打井吧。”
老鼠四接着说:“俺想秋后给老鼠旦娶媳妇,买了几根檩条。如果打井急用,就先拿去。”
又有几户报名的,有的出檩条,有的出砖,但数量都不大。
“韩社长,这事你该带个头吧?”旮旯里不知谁这样问了一句,大家的目光唰地投向了韩天寿。韩天寿本来没想集资,现在见人们都瞪着眼看他,要不说个长短没法交待。于是说:“打井是好事,我全力支持。”
“韩社长,别光磨嘴皮子呀,来实的吧。你说拿什么?拿多少?”
一较真韩天寿噎住了。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觉得农业社是个填不满的坑,扔进多少也是白扔。
石大夯见韩天寿抓着脑瓜皮不表态,也没勉强。他问大家:“还有人报名吗?”
这时何春秀站起来说:“俺娘家为帮我们翻盖房子,送给我两间西房的檩条。现在社里急着打井,就先拉去用吧。”
李贵九立马表态:“这檩条是桥头村的,咱们不能用。”
李碾子不满地瞪了春秀一眼,春秀没理他:“这事我说了算!”碾子不再言语了。
石大夯想,别看来的都是户主,有的在家却做不了老婆的主,不敢表态。为了打破僵局,就说:“这事不一定现在就表态。大伙儿回去商量商量。有多拿多,没多拿少,多少不限。我再强调一下,这是社里借的,不白用大伙的。”
会议开到这份儿上,只好散了。
人们走后,李碾子抱怨大夯:“这么办不行。”
“怎么不行?”
“大夯,你看见了吧?贫下中农家里并不咋的,对打井的事倒挺积极;一些沉实户却往后抽,生怕社里沾他们一层皮似的。光强调自愿不行。”
“你说怎么办?”
“按劳力摊派。”李碾子早就成竹在胸了。
“按劳力摊派?”石大夯在认真思索着。
“对,碾子这主意好,谁也不会有意见。”韩天寿接腔说。
石大夯不同意这么做,摇摇头说:“各户情况不一样,如果均摊,有的户没问题,有的户就会做别子。”
“那你说怎么办?”李碾子急了,“靠自愿,自愿的不多;说摊派,你又不同意。”
石大夯也抓开了脑瓜皮,他确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韩大有说:“按劳力摊派,一个劳力也摊不了多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