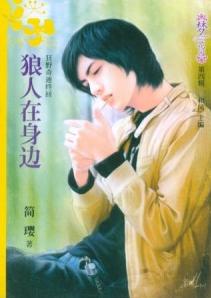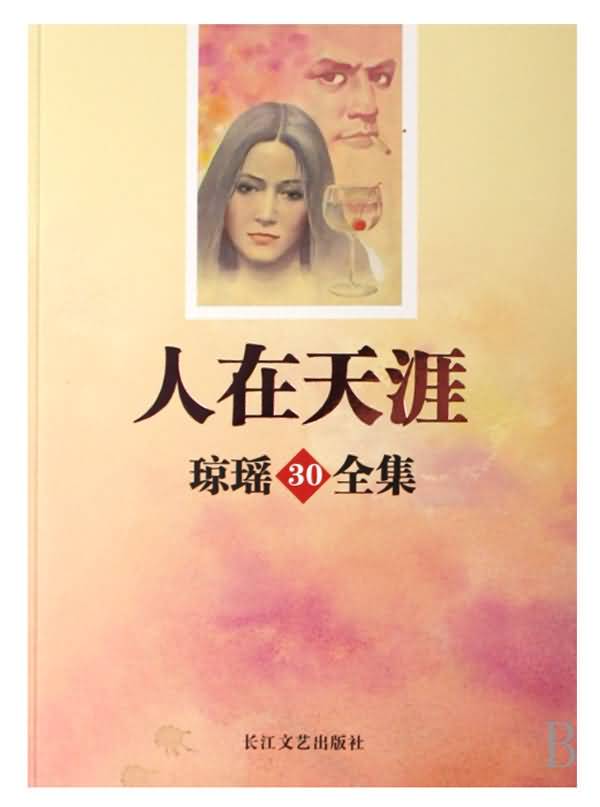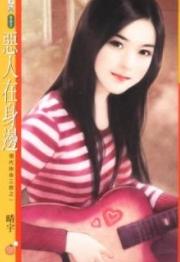人在胡同第几槐-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为除夕的一大亮点。
五十七年前,随父母初到北京,我还赶上过踩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型四合院里,那是机关宿舍,虽然分住了很多家,却俨然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除夕夜,院里的孩子们从大人那里得到压岁钱以后,都纷纷跑到胡同里乃至胡同外的街市上,买到自己喜欢的耍货零食。记得我买的是可以在地上拖着走的兔儿灯和什锦冰糖葫芦。有的小伙伴买的是木制关公刀和糖瓜儿,或者是手提猴戏傀儡和体积十分夸张的棉花糖……年饭后已经放过几阵炮仗、礼花,子时将临又掀起一番放炮放花的高潮。但真到零点来临,则大人们纷纷嘱咐孩子们暂停放炮,全院的人们都集中到院落前边,从院子的二道门——一座精致的垂花门——到斜对着它的大门口,地上满铺着芝麻秸,大人小孩一齐踩岁。那芝麻秸被踩碎的破裂声尽管远不如炮仗响亮,但噼噼剥剥的十分有趣,而且与大人们“岁岁平安”的笑语和孩子们跳跃拍掌的欢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浓酽的过年喜气。
压岁完了踩岁,踩岁完了跟大人一起在家里守岁。那时候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并不普及,但听大人讲各种掌故,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胜过看电影、翻小人书。屋顶挂下萧何不停地追韩信的走马灯,地板上停着被蜡焰照得雪白透亮的兔儿灯,记得母亲就坐在灯之间,告诉我踩岁其实应该写成“踩祟”,就是把坏东西踩掉轰走。她说,你们那么喜欢过年,知道“年”是什么吗?原来“年”就是个“祟”,是个没头没脸的大怪物,每过十二个月它就要跑来一次,必须把它撵跑,放炮仗的目的在于此;踩麻秸的目的也在于此;把它撵跑了,也就“过年”了。听了这样的解说,小小的心里,全然没有对“年”的恐惧,反而呆想:这“年”可别跑远了啊,它常来多好啊,我们随时可以“过年”,也不用再上学了,压岁钱领了可以再领。原来攒一套梁山好汉的“洋画儿”(即夹在香烟盒里的烟画)得费一整年的时间,每月过年那就很快能攒齐了!但是父亲偏乐呵呵地走过来纠正母亲,说把“年”当成怪物对待,那说法至少在明清以后就不时兴了;为什么要踩麻秸?一来芝麻开花节节高。花果熟裂抖出芝麻以后,那些“小铃铛”又让人联想起小元宝,而且芝麻秸不是圆形而是带棱的,风干后踩起来声音特别脆响,所以有“岁岁平安”的含义。二来麻秸挺直,一般总有一米多长,象征“长命百岁”。人们一边踩岁,也就一边祈祝自己一年更比一年好,能够长远地丰衣足食,“脆脆生生”地过好日子。
马君听了我的回忆,拊掌喟叹,说那是建国之初吧?他的父母当时也为新*主义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啊。记得那时候看国产电影,片头是工农兵的雕像在明快的乐曲中缓缓旋转,他哼出那乐曲的头几个音节,我随着延续。那乐曲就叫《新*主义进行曲》,贺绿汀谱曲。在那样的氛围里踩岁,人们心中都怀着无限的憧憬啊。我们聊得正欢,村友三儿从厨房出来——他来给我送自家树上的柿子,刚把那些大柿子摆放在我厨房窗台上——听见话茬就问:什么是新*主义啊?我和马君就齐声让他去读毛泽东的宏文《新*主义论》。三儿一脸不解,马君就说,其实,那意思就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差不多。马君叹息:可惜后来走了弯路,还“大破四旧”,连踩岁的好民俗也给破没了。三儿四十郎当岁,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少年郎,他说一九八○年春节的时候,他爷爷还活着,他家踩过岁,他还有印象,那时候他家房子还没翻盖,睡炕,踩完的麻秸正好放进灶眼里,燃起来又是一片“岁岁平安”的吉祥之音。
我说真想踩岁,只是如今哪儿找芝麻秸去呢?三儿说他们村原来没少种芝麻秸,他爷爷说早年还用大车把芝麻秸和松柏枝、野蒿子运到城里当年货卖。我当年参与的踩岁活动的那些芝麻秸,应该就是院里大人们合伙从三儿爷爷那样的农民手里买来的。马君就问三儿还能不能从村里找到芝麻秸?三儿挠耳朵说,今天开发明天开发,咱们村还剩多少地?花椒树砍光了,没人种芝麻了。也许远处的村里还有人种芝麻。
但是春节前我来到温榆斋,忽见门侧整整齐齐码着一摞芝麻秸。不消猜,一定是三儿想方设法给我找来的。今年除夕我可以约马君来一起踩岁了!望着那摞麻秸,我想,踩岁的意义,起码于我,是提醒自己什么事都急不得,大步跨进什么、跑步进入什么,结果欲速则不达,任何方面的“大跃进”都不可取。不追求夸张虚饰的“大满贯”, 拭心灵,除戾气,实打实地稳步朝前推进,尽可能把失误减少到最低,在平安、平和乃至平常、平淡中享受生活,也许,便自己有福,并能融汇进大家共同的福祉之中吧!
。 想看书来
舞龙尾
在农村书房温榆斋,我问村友三儿他们村过年为什么不舞龙?他说二十几年前舞过,后来兴许是电视呀、网络呀什么的越来越发达,又没有人张罗,所以没人玩了。他建议我去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度假村看舞龙,我知道,那里只要游客多,就必有舞龙表演,也不光是舞龙,还有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抬花轿等许多名堂。他们村里有的村民就被招聘去,在那里上班,舞龙什么的成为一种计时挣钱谋生的手段。三儿作为机务队开大农机的驾驶员,眼下用武之地越来越少,许多农田被征用、被开发了,他那营生也成了“夕阳行业”。他说那个度假村也曾来他们村招人,同龄人有的去了,挣的不算少,也动员他去加入舞龙队,他说他去看过几次,不羡慕,不动心,就还是开大农机。
但三儿回忆起二十几年前参加舞龙,却极为兴奋,声量也高了,脸膛也亮了。他说那时候舞龙根本就不为赚钱,村里有自动挑头的,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男子汉自愿参加,大家凑钱买布,买铁丝,以及其他必备的材料,自己制作长龙,一些娘儿们也兴高采烈地参加进来,用布头拼成龙鳞细心贴上。完工那天,先在村街上拉直了展示,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围观,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辈人,拿着海笔给龙点睛。笔一点,锣鼓齐鸣,炮仗冲天,欢声一片。
他记得,龙头是由村里最强壮的一位大叔掌执,然后一顺全是壮汉和精豆子般的小伙排列在后,每人掌执一段。他呢,当时刚二十出头,被安排在龙尾的位置。他说你可别小瞧了这舞龙尾的,龙头前还有个举着大海珠的,龙头追叼海珠,那当然是大家伙最喜欢观看的。但龙身子的曲折舞动,还有龙尾的摆动,也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才能让观看的人觉得真是蛟龙出海逛到咱们村来啦!
三儿说得我好馋。真想一睹那村中舞龙的盛况啊!
我跟三儿说,舞龙这民俗起源得特别早,有个说法,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蛟龙生于大海,而我们中华大地的水域,黄河也好长江也好,甚至于我们眼前的潮白河、温榆河,在我们先民的心目中,都是与海相通的,一个猛子扎下去,不管是哪条河哪片湖,最后都可以游到龙宫啊……可见水与我们民族生长的关系太密切了!舞龙,应该就是搬出龙王爷来,朝天求雨啊!
三儿对我这一番感慨,毫无共鸣。他说北京郊区,特别是他们这一片地方,从来都是不怕旱,倒是特别怕涝,从老辈子算起,村民就从来都没有求雨的心情,他们舞龙,没有丝毫祈雨的动机。
啊!那我就细问,你那回舞龙尾,究竟是那一年?是不是欢庆改革开放新阶段?是不是因为新的农村政策允许农民离土?是不是刚刚享受到初步富裕的甜头?……三儿不解地望着我,憨憨地说:“刘叔,你跟我聊这些个事,咋总是想掏腾出那么多的大意义来呢?!”
总愿意从一件事情里掏腾出意义,确实是我经常性的思维习惯。回想去年初夏去俄罗斯,先看见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勇士格奥尔基刺杀凶龙的古画,后来到了新建成没多久的胜利广场,那中心的大雕塑,也是勇士持剑把凶龙斩成几截的造型,就更觉刺眼。当然,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凶龙,跟我们民族所幻想的龙,在形象上还有所不同。冷静下来一想,真不该钻牛角尖。美国又在大选,所谓驴象之争,美国*党居然把驴当成自己的美好象征,而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不要说拿驴比喻政党绝对是污蔑,说谁是驴那肯定是谩骂。一个村有一个村的风俗,一个店有一个店的招牌,各村各店无妨各保其固有传统,而又尊重对方,和谐相处。
三儿说,那回舞龙,对他来说,就是特别高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舞龙尾,他紧跟着舞前一段的哥儿们,步法潇洒,腰肢灵活,跃进时觉得自己身子开成一朵大花,暂停时不住扭动双臂表示龙尾欢摆,更觉得自己这朵花在结成一个大果子!
啊!生命中那纯净的高兴,与概念化的意义无关,与收入支出无关,与美食烟酒无关,与情爱和*无关,就是生命自身的花果在欢腾!
愿三儿和我,能在生活的新进程里,获得如他那回舞龙尾般的最单纯的快乐!
玉带林中挂
早在一九八四年,周汝昌先生就发表了《冷月寒塘赋宓妃——黛玉夭逝于何时何地何因》一文,提出了曹雪芹对黛玉的结局设计是自沉于湖的观点。我在《揭秘〈红楼梦〉》的系列讲座和书里,承袭、发展了周先生的这一论断,主要是从古本《石头记》前八十回的诸多伏笔里,探佚出曹雪芹在已经写成而又不幸迷失的后二十八回里,安排黛玉在中秋夜沉湖而逝。整个过程构成一次凄美的行为艺术,体现出黛玉生既如诗、逝亦如诗的仙姝特质。
周先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黛玉沉湖说,似乎关注者不多,经我在《百家讲坛》弘扬后,反响开始强烈。质疑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黛玉葬花时,她否定了宝玉提出将落英撂到水里的建议:“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浑倒,仍旧把花糟蹋了……”她主张土葬,令花瓣在香冢里日久随土化掉。黛玉对落花尚且主张土葬而拒绝沉水,她怎么会到头来自己去沉湖呢?第二个问题是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册页里,画着写着“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如果说后一句意味着宝钗最后孤独地死在雪天,那么前一句是不是意味着黛玉最后是用玉带挂到树上,上吊自尽呢?
正如蔡元培先贤所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每一位红迷朋友,都有参与讨论、独立思考的权利。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提供我个人的看法如下,仅供参考。
黛玉是仙界的绛珠仙草,追随神瑛侍者下凡,她将其一生的眼泪,用以还报后者以甘露灌溉的恩德,眼泪流完以后,她当然就要回归仙界。黛玉沉湖,最后不会留下尸体,不存在像落花一样流出大观园去的可能。当然黛玉在回归仙界前,她又是个凡人,她被赵姨娘通过贾菖、贾菱配制的慢性毒药所害,她在《葬花词》里唱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也向往能够入土为安,但是,“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凡间的险恶令她无法获得“香丘”。因此,在贾母去世、病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