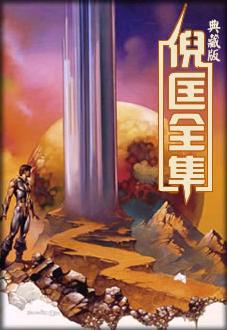后备-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我在看了十分钟之后,实在忍不住,先是轻轻咳嗽了一声,然后,我道:“朋友,你在干甚么?”
我一开始弄出声音来,那人就陡地转过头来,盯住了我,一动不动,那神情,十足是一头受了惊了小动物。我怕他进一步吃惊,所以向后退了两步,再向他作了一个表示友善的手势。
那人在我向后退的时候,动作相当缓慢地站了起来。直到这时,我才看出,他的身形,高大魁梧,看来像是亚洲人,肤色相当黑,眼睛也比较深,貌相很神气,可是神情却极其幼稚。
这人穿著一件看来极其可笑的白布袍子,以致好好的一个人,看起来像小丑又不像小丑,有种说不出来的滑稽味道。
当他完全站直了身子之后,看他的表情,像是想笑,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才好,十分紧张,有点手足无措。
我只好再向他作一个手势:“你好。”
那人的口张动了一下,可是却没有声音发出来,而且在刹那间,他忽然又现出了极其惊惧的神色来,连连向后退。
他退得太急了一些,以致一下子,不知被甚么东西绊了一下,背向灌木丛,仰跌了下去。我一见到这种情形,忙跳过去扶他,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臂。
谁知道我好意的扶持,却换来了意料不到的后果,他忽然发出了一下怪叫声,听来十分骇人,我还未曾明白他为甚么要怪叫,手背上陡地一痛,一时之间,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竟然正低著头,用他的口,在狠狠咬我的手背。
当你的手背被人咬的时候,唯一对付方法,当然是立即捏住咬人者的腮,令他的口张开来。我当时就是这样做,而且,当那人的口被我捏得张了开来之后,我还挥拳,在他的下颚上,重重击了一拳。这一拳,打得那人又发出了一下怪叫声,跌进了灌木丛中。
我摔著手,手背上的牙印极深,几乎被咬出血来。我心里又是生气,又不明白正想向那人大声喝问之际,两道亮光,射了过来。
我看到一辆车子,向前疾驶而来,车子的速度相当快,一下子就驶到了近前,自车上跳下了两个人,直扑灌木丛。
那两个人的动作十分快,一扑进灌木丛中,立时抓住了那个人,那个人发出可怕的呼叫声,挣扎著,但是却被那两个人拖出来,拉向车子。而在这时候,我也已看清了,那辆车子,正是丘伦的照片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轻便车。
那两个人自然也看到了我,他们向我瞪了一眼,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我看他们已经将那人拉上了车子,两人中的一个已经跳上了驾驶位,我忙叫道:“喂,等一等,这个人是甚么人?”
那个驾车的粗声道:“你以为他会是甚么人?”我扬著手:“他咬了我一口。”
那个人闷哼一声,不再理我,车子已向前驶去,我立时跟在后面追,车子去得很快,我追到一半,便不再追车,而奔向我自己的车子,等我上了车,发动车子,还可以看到那辆车子的灯光,我驾著车,以极高的速度,疾追上去。
那辆车子,驶近疗养院,从自动打开的铁门中驶进去。我的车子跟踪驶到,铁门已经自动关起,我若不是停车停得快,几乎直撞了上去,紧急煞车的声音,划破了静寂,听来十分刺耳。
我先不下车,在车中定了定神,一切事发生得太突然,叫人无法适应。我只可以肯定一点:这个有著高得不合理的围墙的医院,一定有极度古怪。
我吸了一口气,下了车,来到铁门前,向内看去。医院的建筑物,离铁门大约还有三百公尺。医院建筑物所占的面积并不大,围墙内是大幅空地,是一个整理、布置得极其美丽的花园,整个花园,纯欧洲风格。在距离铁门一百公尺处,是一圈又一圈玫瑰花,围著一个大喷水他,喷水池的中心,是一座十分优美的石像。
建筑物中透出来的灯光不多,花园更浸在黑暗之中,看来十分宁谧,全然不像有甚么变故发生过的样子。我略为打量了一下,就伸手去按铃。
我才一按下铃,就听到门铃旁的扩音机,传出了一个听来很低沉的声音:“甚么人?甚么事?”
我吸了一口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我采用了最审慎的态度:“我是一个过客,刚才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想找你们的主管谈谈。”
我一面说,一面打量著铁门和门栓,立即发现有一具电视摄像管,正对著我,可知和我讲话的人,可以在一具萤光屏上看到我。
我以为,我说得这样模糊,对方一开始语气就不怎么友善,我的要求一定会被拒绝,谁知道对方只是停了极短的时间,就道:“请进来。”
他答应得那样爽快,倒令得我一呆,可是我已没有时间去进一步考虑,因为铁门已自动打开,我道了谢,走进铁门,门立时在我后面关上。
在我的想像之中,这座医院既然有古怪,我走进去,一定会有十分阴森诡秘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却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月色之下,经过刻意整理的花园,处处都显得十分美丽。
当我走过喷水池时,已看到医院的大门打开,一个穿著白袍的人,向我走来。当我们相遇时,那人伸出手来,说道:“你是将军的保镖?”
我怔了一怔,反问道:“齐洛将军?不是,我和他唯一的关系,大约只是我们全是亚洲人。”
那人呵呵笑了起来:“那我犯错误了,不该让你进来。”他讲到这里,又压低了声音,现出一种十分滑稽的神情:“齐洛将军要求我们作最严密的保安措施,我们医院中的病人,尽是显赫的大人物,但从来也没有一个比他更紧张的。”
这个人,大约五十上下年纪,面色红润,头发半秃,一副和善的样子,给人的第一印象,十分良好。
我和他握手,他用力摇著我的手:“你说刚才遇到了一些不可解释的事?那是甚么?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体,降落在医院的屋顶?”
他说著,又呵呵笑了起来,我只好跟著他笑:“不是。”
他问道:“那么是──”
我把我在湖边见到的事,向他说了一遍,那人一面听,一面摇著头:“是的,我们的一个病人,未得医生的许可,离开了医院的范围。”
我道:“一个病人?”
那人道:“是的──哦,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杜良医生,乔治格里·杜良。”
他好像很希望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甚么人,可是,我对医药界的人士熟悉程度,还没有到这一地步,所以我只好淡然道:“医生。”
杜良医生的神情多少有点失望,他继续下去:“这个病人,你多少觉得他有点怪?他患的是一种间歇性的痴呆症。这种病症,十分罕见,发作的时候,病人就像白痴一样,要经过长时期的治疗,才有复原的希望。”
杜良医生在开始说的时候,已经向医院的建筑物走去,我跟在他的身边。等到他讲完,已来到了门口,他向我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看他的神情,全然不像是对我有甚么特别防范。而他的解释,也十分合情合理,我也应该满足了。如果不是有丘伦的死亡一事在前,我可能就此告退。
我在门口,略为犹豫了一下,杜良扬了扬眉:“你不进去坐坐?”
我道:“不打扰你的工作?”
杜良摊开了手:“轮值夜班,最希望的事有人来和你闲谈,你是 ”
我向他说了自己的姓名,虚报了一个职业,说自己是一个游客。杜良摇著头:“别骗人,游客怎么会到这里来?我看你,是一个太热心工作、想采访一点独家新闻的记者。”
我只好装成被他识穿的模样,尴尬的笑了一下。杜良十分得意地笑著。我们走进建筑物的大门,门内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堂,一边是一列柜台,有一个值夜人员,正在看小说。
我不厌其烦地形容医院内部的情形,是因为这家医院,虽然我认定了它有古怪,可是从外表看来,它实在很正常,和别的医院全无分别。
杜良带著我,转了一个弯,进入了一间休息室,从电热咖啡壶中,倒了一杯咖啡给我:“我只能告诉你,齐洛将军的健康十分良好,可以在最短期内出院,回国重掌政务。”
我不是为了采访齐洛将军病情而来的记者。我的目的,其一是想看看这间医院内的情形,如今看不出甚么异状。第二,则是想在杜良的口中,套问出一点我想知道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丘伦多年前在湖边的遭遇,所以我一听得他这样说,立时凑近身去,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来,压低了声音:“齐洛将军这次是公开就医,但早五年,他曾秘密来过?”
杜良呆了一呆:“没有这回事。”
我伸手指著他:“你在这里服务多久了?要是超过五年,一定知道,请不要骗我。”
杜良道:“我在这间医院,已经服务超过了十年。”
我打了一个哈哈:“那就更证明你在骗人,我有一个朋友,五年前,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湖边,看见过齐洛将军,还拍下了照片。”
杜良皱著眉,瞪著我,看他的神情,像是听了甚么极度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多一会,他便恍然大悟笑了起来,用力一拍他自己的大腿:“对了,那时,将军还不是甚么特别显赫的人物,所以我记不起他,他好像来过。”
杜良从一出现开始,给我的印象就不坏,他爱呵呵笑,说话的态度也很诚恳,而且主动请我进医院的建筑物来,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
可是这两句话,却令得我疑云陡生。
如果有一个病人,几年前来过,现在又来,正在接受治疗,绝无可能由于这个病人上次来求医时地位不是十分显赫,而忘记了这件事。
杜良的这句话,明显地表示:他是在说谎。
他为甚么要说谎?企图隐瞒甚么?我迅速地想著,不拆穿他,只是随口附和了几句:“我那位朋友,就在他看到齐洛之后的相当短时间内,被人谋杀,你有甚么意见?”
杜良的回答倒很得体:“我能有甚么意见?”
我盯著他:“我想,他是由于发现了一个极大的秘密,所以才招杀身之祸。”
杜良神情感叹地道:“是啊,探听别人的秘密,是一个坏习惯──”他说到这里,伸手向我指了一指:“对健康有害。”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四面看看,杜良道:“你认为我们医院中有甚么秘密?”
我故意道:“那也难说得很。”
杜良又笑著,凑近我:“据我知道,在地下室,正在制造吸血僵尸、科学怪人,还有鬼医,你可真要小心一些才好。”
我道:“好笑,很好笑。”我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我要走了。”
杜良一直陪著我走出了医院的大铁门,看著我上了车。
如果不是杜良的话引起了我怀疑,我真可能就此离去,另外循途径去调查丘伦的死因。但这时,既然有了怀疑,自然不肯就此算数。我驾著车向前驶,肯定杜良看不到我了,才停车熄灯。
四周围十分静,我在车中静坐了片刻,将发生在丘伦身上的事,和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又仔细想了一遍。仍然觉得那座勒曼疗养院可疑。但是究竟可疑在甚么地方,我却也说不上来。
我停了几分钟,就下了车,循原路走回去,看到医院的围墙时,我的行动十分小心,尽可能掩蔽著前进。
到了墙脚,贴墙站定,抬头向上看去,约有八尺高的围墙,看来十分异样。我不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