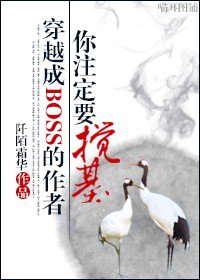闯关东 作者:高满堂 孙建业-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秀儿说:“老虎长两只尾巴?怎么回事?你讲,快讲啊!”
传武说:“那一年我在山场子干活,我们的把头叫老独臂。老独臂嘛,当然就有一只胳膊。你知道他那只胳膊哪儿去了吗?”
秀儿说:“不知道。”
传武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说:“你听我讲。那一年老独臂在老林子里遇见了一只老虎,一只斑斓猛虎,那老虎看样好多日子没吃食了,肚子溜瘪。老虎看见了老独臂嘿嘿笑了。”
秀儿说:“我不信,老虎还会笑?”
传武连说带比画道:“老虎是在心里笑,嘴里没笑出声来。老独臂一看,坏了,怎么遇见这么个倒霉旋儿,肚子溜瘪,看样是出来下馆子!老虎拿眼斜楞老独臂,心里的话,这个老干柴棒子,瘦了点,老了点,拿他当点心小心塞牙。老独臂寻思,不能跑,一跑老虎就知道我怕了,撵上来咔嚓一口我的头就没了,先下手为强吧,亮亮我的真功夫,耍了一套通臂。老虎在那儿纳闷儿:莫非这老头是哑巴?给我打手语?我也不懂啊!摇了摇头。老独臂误会了,心里话,你不服是吧?看这个。又耍了一套螳螂拳。老虎还是摇头,心里说,别和我废话了,下手吧,嗷的一声就扑过来了。老独臂一看急了,你怎么不按套路来?哪个师娘教的!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就来咬老独臂。老独臂也是急了眼,就势把胳膊捅进老虎嗓子眼儿里了。老虎噎得直翻白眼儿,心里的话,你这是什么套路?可到底把老独臂的胳膊咬掉了。老独臂一看,娘的,吃亏的买卖咱不能干,不能折本儿!忍着痛把手里的木棒捅进老虎屁眼里。老虎觉得屁眼里火烧火燎的,没尝过这滋味儿,吼又吼不出来,撒欢儿跑了。”
秀儿咯咯笑着说:“这下老虎可吃大亏了。”
传武说:“可不怎么的。老虎也找不到先生瞧病呀,忍着痛在老林子里到处溜达。约摸半个月以后吧,老独臂见老虎死在林子里。老远地看着老独臂就奇了怪,这老虎怎么长着两只尾巴?近前一看,哈哈,一只是真尾巴,另一只是他的那根木棒,还插在老虎的屁眼里呢!”听到这里,秀儿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朱开山与文他娘听着从新房里传来的笑声,欣慰地笑了。
朱开山说:“这孩子,多少年没看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个媳妇拴着,他的野性慢慢地就收了。”
文他娘说:“也不见得,生姜断不了辣气,你年轻的时候倒有老婆拴着了,可你要跟着义和团闹事,我拴住你了?”
传武越讲越有精神,而秀儿激动加劳累,渐渐地闭了眼睛,依偎在传武的怀里进入了梦乡。传武这才闭了口,小心地把秀儿放在床上,自己蹑手蹑脚地打开床头的衣柜,随便翻了几件衣裳,用一块包袱包起来,悄没声地出了屋。月近中天,满天的星光。传武呆呆望着天空,好一会儿,他回过神来,听听左右厢房一片静谧,自己一闪身进了鲜儿的屋。
鲜儿仿佛在等他来,默默地坐在炕头上,其实这一夜她又何尝合过眼啊!
传武一笑说:“我就知道你没睡。”
鲜儿淡淡地说:“我就知道你会来。”
传武小声地说:“姐,我备了马,赶快,和我一块儿走!”
鲜儿问:“上哪去呀?”
传武说:“关东山天高地远,有的是地方,咱俩放排去,快活去,天管不着地管不着,那才是咱们该过的日子!”
鲜儿说:“啊?原来你是诓了爹,你一走这个家怎么办?秀儿怎么办哪?”
传武说:“顾不了那么多了,这都是叫爹逼的!快走吧!”
鲜儿心里头纷乱,态度却坚决,说:“不,我不走,走了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传武说:“你不走也能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不走也得走!”
不由分说,拖着鲜儿出了屋。鲜儿还要再说,传武使出了浑劲:“你喊吧,你这时候把他们喊醒更说不清。”
传武从马厩里牵出平日里骑惯了的红马,紧紧攥着鲜儿的手,就此出了院。一出村口上了大路,他立即纵马在桦树林边的原野里飞奔起来。
传武快活地叫着说:“啊!可是自由了,谁也别想再管我了!”
鲜儿疲惫地倚在传武的怀里,轻声地说:“传武,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咱们这一走爹娘非得急疯了不可!”
传武勒住马,转身朝着家的方向,大声地快活地喊着说:“爹、娘、秀儿,传武对不起你们啦!鲜儿跟我在一起,你们就放心吧!”
第十六章
1
朱开山直奔桦树林中鲜儿住过的木屋,他抡着棒子把屋里的坛坛罐罐砸得稀里哗啦。传文默默地看着。朱开山砸够了,自己停下来,大口地喘着粗气。
传文小心翼翼地将他扶坐在门前,劝着说:“爹,行了,他们不会回这儿了,咱别处找找吧。”
朱开山老泪纵横道:“老大,爹丢不起这个人啊,真想一头撞死!爹杀过洋毛子,老金沟和官兵斗,和马贼斗,飞镖毙了老果子的命,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可今天就败在这个逆子手里,我的心里过不来呀!”
传文说:“爹,父子爷们儿没有输赢,别往那儿想,咱还是去找他吧。”
朱开山伤感道:“不找了,关东山地方太大了,他要是不想回来,找是没用的,想想怎么对付韩家吧,这个坎儿可不好迈呀!”
秀儿木然地坐在新房的炕头,无声地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窗上的大红喜字。门响了一下。秀儿抬起头,竟然是一郎。
秀儿擦了擦眼泪,轻声地说:“一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快睡觉去!”一郎站着不动。
秀儿说:“听见没有?睡觉去!”
一郎像没听见一样,慢慢地向前挪了两步,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块手绢,塞在秀儿的手里,慌张地转身跑了。秀儿看着手绢,默默地擦着眼泪。
秀儿还是回了家。韩老海在地上踱着步,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咆哮着说:“朱开山他不叫玩意儿!他这是耍笑我,羞臊我,撕下我的脸皮扔到脚下踩,还蹍了又蹍。闺女,我非把这口恶气出了不可!我要是再不放个屁,在元宝镇就没法见人,元宝镇的狗都会笑掉大牙!我这就去找他!”
韩老海领着亲戚,伙计们抄着家什,气势汹汹打上了门。朱家所有的门窗都大开着,朱家所有的人都老老实实地站在院子里,一言不发。一郎偎在文他娘的怀里,满脸惊惧。
韩老海红了眼,发一声喊道:“给我砸,狠狠地砸!”
顿时稀里哗啦,响成一片。传文急了眼,朱开山一把拽住他。
韩老海不管这套,举起镢头,“砰”的一声,把朱家的锅砸了。传文喊着说:“爹,他们欺负人欺负到家了,我和他们拼了!”
朱开山轻轻抬手,一下子把传文撂倒在地,喝一声道:“谁要敢动一下我叫他这一辈子别起来!”
那文赶忙过来扶起传文,瞪着公公却不敢言。一会儿工夫,朱家被砸得一片狼藉。
文他娘发话了说:“亲家,气撒完啦?”
韩老海气咻咻地说:“朱开山,咱两家没个完!”一挥手说,“伙计们,这是头一回,让他们收拾收拾,明天还来!”
韩家的人走了。
全家人都看着朱开山,却又不敢说什么。
朱开山沉默良久道:“传文,你到韩家递个话,今天晌午我在镇上酒馆请他喝酒说话,请他务必赏脸。”
传文哭着说:“爹,他把咱家的锅都砸了,这跟掘咱祖坟一样啊,凭什么还请他喝酒!”
朱开山说:“唉,这件事说到天边咱也亏理,要是摊在咱身上这也解不了气,将心比心吧。我和他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传文说:“那咱就忍了?”
朱开山长叹一声道:“咱山东人闯关东,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吃不容易啊,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关东苞米,就咱一棵山东高粱挺在地里,孤木不成林,要万事小心!”
朱开山在元宝镇的一个酒馆里坐等韩老海。韩老海依旧气势汹汹领来了镇里有威望的老人和一些窜地龙(东北土语,恶棍),众人一屁股坐下。
朱开山起身抱拳说:“亲家,消消火吧,咱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肝火大了伤身。我朱开山现在立在这儿,可心里是在跪着和你说话。儿女大了不由人,我们朱家对不住你,更对不住秀儿,你想怎么着我都认了,决不说二话。”
韩老海火气冲天道:“朱开山,你们家还叫人吗?传武跑了,我闺女怎么办?还嫁不嫁人了?嫁人能嫁出去吗?不嫁人叫她这辈子守活寡吗?啊?”
朱开山说:“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等我抓住这鳖羔子,当着你的面活生生地劈了他!”
韩老海说:“哼!都说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你朱开山就是这样教儿育女的?”
朱开山不停地点头认罪说:“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
一个老人不忿道:“你们山东人就是嘴会说,满口的仁义道德,可做的事呢?够评的吗?你们跨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啊,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元宝镇你们说了算了?我看这件事就是不公。”
窜地龙龙小三拍着桌子说:“我他妈就看着不公!传武这鳖羔子,别叫我碰上,要是让我挠着,非捆到林子里让野兽分尸不可!”
另一个干脆揪住朱开山的脖领说:“还抓他的儿子做什么?今天先把他老子教训教训!”
朱开山怒喝一声道:“混账!这儿没你们这些窜地龙说话的份儿!”
话毕,暗运掌力,向下拍去,只听“呯”一声一掌把酒桌砸趴下了,酒菜洒了一地。
众人被朱开山的神力震慑,脸色大变。韩老海神色尴尬地溜走了。
这个当,一个韩家的伙计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不好了,秀儿跳井了!”
朱开山和韩老海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说:“啊!”
来人大喘了几口气说:“还好,救过来了,老韩叔,你快回去看看吧!”
2
过了有半个月,朱家日子才算安生点,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平稳饭。
文他娘说:“唉,这些日子叫传武的事闹腾得不轻,一家人没好好吃顿饭,这才安稳了点,赶明儿咱烙葱花大油饼。”
那文嘴甜说:“娘,我拉风匣。”
文他娘说:“你也就会拉个风匣。”
那文笑道:“娘,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文他娘说:“拉倒吧,就你这份火头军?拉起风匣来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像月孩子抽风,不稀说你。”
传文说:“娘,咱家的风匣不好使,也怨不得那文。”
文他娘说:“你看看,一说你媳妇你就护着。咱家的风匣怎么不好使的?生生叫你媳妇拉坏了!娘耶,她那叫拉风匣?赶上拉大锯了,呼嗒嗒,呼嗒嗒,咬着牙闭着眼,像是跟谁有仇。”
朱开山威严地说:“行了,吃顿饭你的嘴拾不闲。一郎呢?”
文他娘说:“咦?刚才还在院里耍,掉腚儿没有了。哪儿去了?”
正说着,一郎气冲冲地走进院,脸上挂着伤,衣服也被撕破了,不停地挥舞着手臂,却不说一句话。
文他娘一愣,问道:“可伤了,俺的老儿,你这是怎么了?谁打的?快告诉娘,是谁?谁下这么狠的手?”
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