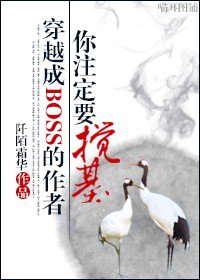闯关东 作者:高满堂 孙建业-第7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垛爷说:“放心吧,亏不了你。”那伙计往前走了。
天黑下来了。张垛爷跳下马背喊了声说:“歇了吧!”马帮停了下来。
一个赶马帮的伙计走到张垛爷跟前问:“张垛爷,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张垛爷说:“那就在这儿打铺睡呗。”
伙计说:“就在这大野地?”
张垛爷说:“大野地咋的?你没睡过?我没睡过?他有人没睡过!”
那伙计明白了,会意地一笑,说:“你是要熬鹰啊!”
传杰赶过来说:“张垛爷,咋也得找个客栈哪。”
张垛爷说:“咋找啊?往前五十里,团山子有客栈,赶到那天都得快亮了,明儿个还咋赶路?往后三十里,榆树屯有店,也得过半夜能到,里外里白走六十里地,划算吗?”
传杰看看四周,说:“这……这冰天雪地的,能睡吗?”
张垛爷说:“赶垛子的哪有那么多娇气,哪儿不能睡?再说了,这也能给你三掌柜的省点儿盘缠钱哪。”
那边,几个赶垛子的伙计已经点起了篝火,铺好了毡子。
张垛爷向他们走去,留下传杰无奈地站在夜幕下。
夜空上寒星闪闪。张垛爷和赶马帮的伙计们已经睡熟了。
传杰和小康子裹着一个毯子,相依而坐,瑟瑟发抖。
小康子上牙直打下牙,说:“三……掌柜的……这……这样可不行……行啊……再……再拢堆火……火吧……”
朱传杰也打着颤说:“对……对对……拢火……火……”
二人起身去拾柴草。躺着的张垛爷睁开他那双小眼睛,向朱传杰和小康子这边看了看。
就这么连着三天,传杰身子撑不住了,呼吸浑重,全身发热,得了风寒。不得已,马帮找了个大店歇下。
小康子找了郎中来抓了几服药。
传杰吃了药盖着大被躺在炕上。小康子拧了一条手巾,敷在传杰的额头。
张垛爷叼着烟袋走进来说:“咋样啊?都躺一天了,误了路程可怨不了我。”
小康子说:“不怨你怨谁?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了哇?”
张垛爷说:“小子,是你没扛得了,还是我没扛得了?谁想到他身子这么金贵!秧子货!”
传杰睁开眼睛说:“还是往前赶吧,兴许,扛一扛这病就好了。”
张垛爷说:“那好,我去张罗上路。”
张垛爷要走,传杰说:“等等。”他挣扎着坐起来说,“小康子,把钱褡拿来。”
传杰说:“张垛爷,往后的路程,一切事儿就托付给您老了。这是我带来的所有的钱,现在都归您掌管,客栈咱找好的住,饭菜咱挑好的吃……”
张垛爷没接钱褡说:“三掌柜的,你这是骂我。”
传杰说:“不,张垛爷,前些天是我少不更事,慢待了垛爷,慢待了诸位弟兄。”他挣扎着下了炕作了个大揖说,“对不住了……”
话没说完,脑袋一沉,人又一头栽倒下去。
张垛爷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塞给小康子,说:“这有几颗药丸子,你一天给他吃一颗,我保他好。”
正午时分,马帮来到一座向阳的山坡。
张垛爷跳下马,冲大伙喊道:“打尖了!”
人们停下来,就地休息。张垛爷把马料口袋扔在马头前,自己坐了下来,掏出烟袋。
传杰走到张垛爷跟前说:“张垛爷,咋不上前边的客栈歇歇?也好让大家吃口热乎的。”
张垛爷说:“你不是让我说了算吗?今儿个老爷儿(太阳)多好,这地场又朝阳,多暖和,赶上小阳春了。”
传杰在他身边坐下说:“张垛爷,我病的这两天,多亏你了。你好客栈不住,还总吃些平常饭菜,也太省了,你可别……”
张垛爷说:“我怕你的钱不足兴。”
传杰说:“我担心您老是不是对我还有……”
张垛爷说:“身子骨刚好一点,就磨叽起来了。你放心,我轻饶不了你,等明天到地方卸了货,再把回去的货装上,我吃死你!”
传杰笑了:“等回到哈尔滨,我还给你摆大席呢!”
张垛爷又装一袋烟说:“你爹送我的这亚布力烟,虽说冲,味儿可真好!”
3
山东菜馆门前的街上,一个报童举着报纸边喊边跑说:“看报!看报!强盗抢劫俄国人,近日就将正法!看报,看报……”
鲜儿一身男人打扮,满脸忧戚之色。她买了一份报纸,上面印着的照片正是她要找的镇三江。
杂货铺的刘掌柜凑过来看报,一惊道:“妈呀,这好汉要没命了?”
鲜儿问:“大叔,你认得这个人?”
刘掌柜说:“前些天,他在这条街上吃过饭呢。”
鲜儿说:“哪家饭庄啊?”刘掌柜指着山东菜馆说:“就那家。”
走进山东菜馆,鲜儿找个位置坐下。
朱传文走过来招呼:“先生,你要些啥?”
鲜儿看着传文,愣住了,颤声问道:“你是——朱大哥?”
传文也愣了,端详着鲜儿的脸说:“鲜儿?”
鲜儿点点头,传文激动得张口就要喊,鲜儿拉住他示意低声。
传文说:“走,上后屋去。”
传文领着朱开山和文他娘进来。
朱开山说:“鲜儿,你果真是鲜儿?”
鲜儿摘下帽子说:“爹……”
文他娘搂住鲜儿,流下眼泪。鲜儿也哽咽说:“娘……”
文他娘说:“快告诉娘,你这些年怎么样啊?过得好啊?”
鲜儿说:“好,挺好的。”
文他娘说:“你男人?”
鲜儿一错愕,随即点头说:“男人?啊,我男人也挺好,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文他娘说:“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朱开山说:“家也在哈尔滨哪?”
鲜儿说:“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个亲戚,路过这儿。”
那文进来了,门口还站着秀儿。
那文说:“鲜儿妹子来啦?我看看,我看看。哟!还是那么俊哪!”
鲜儿说:“俊啥呀,都老太太了。”
文他娘说:“你是老太太,那我呢?”
鲜儿看到了门口站着的秀儿。秀儿看着她,眼里似有怨恨,一声没吱。
鲜儿说:“爹,娘,我该走了。”
文他娘说:“才来就走哇?在这儿多住几天呗。”
鲜儿说:“家里人该着急了。改天吧。”
鲜儿走到门口,停下来,看一眼秀儿,说:“秀儿,姐姐对不住你。”说完掩面跑出去。
文他娘朝朱开山说:“我看鲜儿不大对头啊。”
朱开山点点头说:“是啊,怎么才进了家,就走了呢?”那文说:“不是说去看个什么亲戚吗?”
文他娘说:“她那亲戚比咱家和她还亲?”
秀儿说:“娘,她是不是还寻思传武死了,觉着对不起咱家啊?”
朱开山思忖着说:“兴许啊!刚才怎么就没空出嘴来,和她把这事说了呢?”
朱开山和传文正在算账。夏玉书拿张报纸走进来说:“爹,我从学校带回张报纸,你看看。”
朱开山说:“你叫我看?你当我也像你似的当老师呢——我才认得几个字儿。”
夏玉书说:“这个人你能认识。”
玉书打开报纸,上面印着大掌柜镇三江的照片。
朱开山说:“是他?”传文也凑过来看。
朱开山指着报纸问玉书:“这上头咋说的?”
玉书说:“他已经被判处死刑。”
朱开山眉头紧锁。传文说:“爹,他说的那几两银子……”
夜里,关帝庙外,弯月当空。关帝庙后的大槐树下,两个黑影在晃动,是朱开山和朱传文。父子二人来到树下,搬开石头。
朱传文摸到了东西说:“爹,有了。”
是个小包裹,传文打开,父子二人一看,竟是金条、元宝、女人用的首饰,还有不少俄国贵族用的金银餐具。
朱开山说:“这要是换成银子,少说也值百八十两。”
传文说:“哎呀,这可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呀!爹,多亏你管了那个人一顿酒菜。咱可以用这笔钱再开个铺面……”
朱开山说:“不!虽说这笔财宝是那好汉的,即便他是将死之人咱也得还给人家。”
传文说:“是该还,可咋还哪?他在死牢里呢。”
朱开山说:“我明儿个把这些财宝拿去换成银子,再找人到衙门口活动活动,整好了呢,兴许能把好汉的那条命换下来。就是换不下来,咱也是把钱还给他了。”
傍晌午,菜馆前厅里客人熙熙攘攘。这时,进来个人,还没等跑堂的上前,他自己便拣了个凳子坐下来。
跑堂的急忙走过来问:“先生,要啥菜?”
来人说:“吃啥呢?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跑堂的愣了一下说:“啥?”
来人说:“你聋啊?大爷要油炸冰溜子!”跑堂的支吾着转身向后厨跑去。
朱开山正在刨井边结的冰。
传文跑过来说:“爹,有客人点了个油炸冰溜子。”
朱开山一怔说:“油炸冰溜子?”
传文说:“爹,有这道菜吗?”
朱开山想了想说:“有,当年我在金场子的时候,听说过这道菜。”他扔下镐说:“走!”
朱开山领着传文回到前厅,那人却不在。
传文问跑堂伙计说:“人呢?”
跑堂的说:“他刚刚出去了。”
菜馆门前围了不少人。那人正踩着梯子,要上去摘幌子。房檐下,挂着一排冰溜子。
朱开山笑了说:“这位朋友,你可真是个急性子啊。点的菜还没吃呢,怎么就开摘幌子了?”
那人说:“咋的?油炸冰溜子你们做得出来?”
传文拿个盆从店里出来。
朱开山仍然笑着说:“朋友,你先别下来,借你个手,帮个忙。”他拿过朱传文手里的盆说,“你就手把那冰溜子掰几个下来。”
盆里的冰溜子被倒上了面糊。旁边的油锅开了,翻着花。传文、那文、秀儿在一旁紧张地看着。朱开山把裹了面糊的冰溜子下到油锅里,稍一炸开便用笊篱捞上来,放到了盘子里。
朱开山把一盘金灿灿的油炸冰溜子放到了那人面前。那人看着盘子,又扭头看朱开山,不大相信,问:“这就是油炸冰溜子?”
朱开山笑着说:“你尝尝嘛!”
许多吃客围过来看稀罕。那人咬一口,冰溜子冒出丝丝白汽。众人无不叫好。
朱开山问那人说:“朋友,以前吃过吗?”
那人摇头。
客人们不忿了,有人喊起来说:“没吃过你耍什么疯啊?”
“你是不是想讹人哪?”
那人讷讷地分辩道:“俺,俺也是受了别人的指派,他说,说你家肯定做不出来……”
众人骂道:“啥人这么缺德呀?”
“要和朱家过不去,你当面站出来呀!”“他就是来摘人幌子的!”
朱开山说:“各位老少,各位老少,先别吵吵。说实话,我还得谢谢这位朋友呢,要不是他今天要这道菜,我还真把这手艺忘到锅台后边去了。”
有人嘀咕说:“这种损事也只有那潘五爷做得出来。”
饭店打烊了,朱家还在议论油炸冰溜子的事儿。
文他娘说:“上回是爆炒活鸡,今儿个又是油炸冰溜子,说不定明儿个又闹出个啥咕咕鸟儿。”
传文说:“爹,是不是咱再多让一步?”